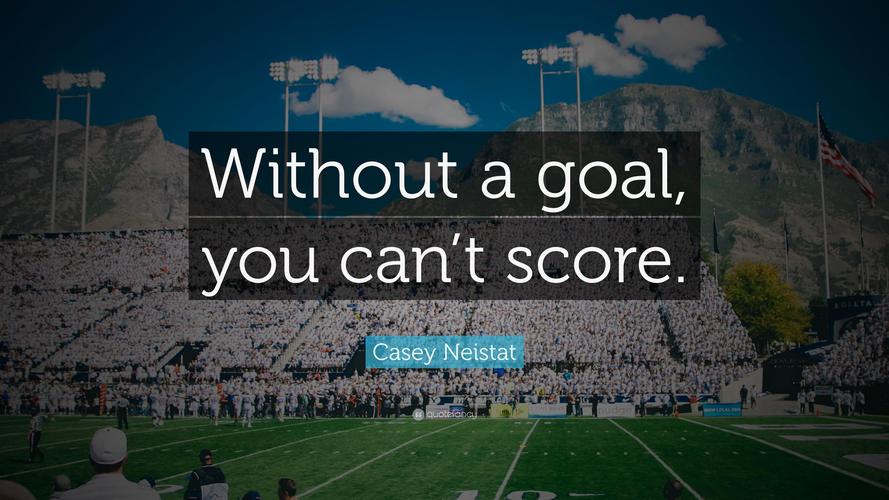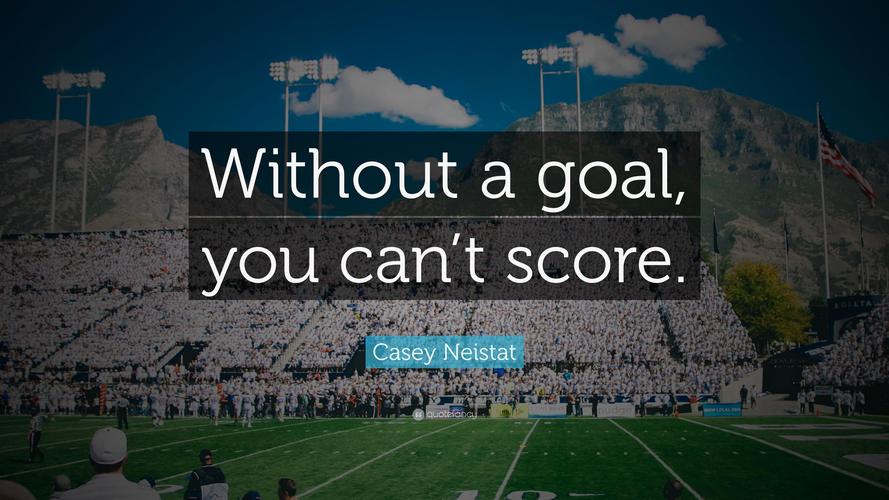
老海棠樹
史鐵生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塊空地,不論窗前窗后,要是能隨我的心愿種點什么,我就種兩棵樹。一 棵合歡,紀念母親。一棵海棠,紀念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樹,在我的記憶里不能分開;好像她們從來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 棵老海棠樹的影子里。
老海棠樹近房高的地方,有兩條粗壯的枝Y,彎曲如一把躺椅,小時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 地就在那兒玩。
春天,老海棠樹搖動滿樹繁花,搖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記得奶奶坐在樹下糊紙袋,不時地沖 我嘮叨:“就不說下來幫幫我?你那小手兒糊得多快! ”我在樹上東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說: “我求過你嗎?這回活兒緊!”我說:“我爸我媽根本就不想讓您糊那破玩藝兒,是您自己非要這么累!” 奶奶于是不再吭聲,直起腰,喘口氣,這當兒就呆呆地一從粉白的花間,一直到無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樹枝繁葉茂,奶奶坐在樹下的里,又不知從哪兒找來補花的活兒,戴著老花 鏡,埋頭于床單或被罩,一針一線地縫。天色暗下來時她沖我喊:“你就不能勞駕去洗洗菜?沒見 我忙不過來嗎? "我跳下樹,洗萊,胡亂一洗了事。奶奶生氣了: “你們上班上學,就是這么糊弄?” 奶奶把手里的活兒推開,一邊重新洗菜一邊說:“我就一輩子給你們做飯?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 作? ”這回是我不再吭聲。奶奶洗好菜,重新撿起針線,從老花鏡上緣抬起眼,又會有一陣子愣愣 地。
有年秋天,老海棠樹照舊果實累累,落葉紛紛。早晨,天還昏暗,奶奶就起來去掃院子,“刷 啦一刷啦一",院子里的人都還在夢中。那時我大些了,正在插隊,從回來看她。那時奶奶一 個人在北京,爸和媽都去了干校。那時奶奶己經腰彎背駝。“刷啦刷啦”的聲音把我驚醒,趕緊跑出 去:“您歇著吧我來,保證用不了三分鐘。”可這回奶奶不要我幫。“咳,你呀你還不懂嗎?我得勞動。” 我說:“可誰能看得見? ”奶奶說:“不能那樣,人家看不看得見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覺。”她掃完了 院子又去掃街。“我跟您一塊兒掃行不? ”“不行。”
這樣我才明白,曾經她為什么執意要糊紙袋,要補花,不讓自己閑著。有爸和媽養活她,
她不 是為掙錢,她為的是勞動。她的成分隨了爺爺算地主。雖然我那個地主爺爺三十幾歲就一命歸天, 是奶奶自己帶著三個兒子苦幾十年,但人家說什么?人家說:“可你還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剝削飯”這 話讓她。她要用行動證明。證明什么呢?她想著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點懂 了:什么時候她才能像爸和媽那樣,有一份的工作呢?大概這就是她的吧,就是那老海棠樹下屢屢 的迷茫與空荒。不過,這或許還要更遠大些一她說過:得跟上時代。
所以冬天,在我的記憶里,幾乎每一個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燈下學習。窗外,風中,老海棠 樹枯干的枝條敲打著屋檐,磨擦著。奶奶曾經讀一本《掃盲識字課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報紙 上的頭版新聞。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寫過:她學《國歌》一課時,把“吼聲”念成了“孔聲”。我寫 過我最不能原諒自己的一件事:奶奶舉著一張報紙,小心地湊到我跟前:“這一段,你給我說說, 到底什么意思? "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學那玩藝兒有用嗎?您以為把那些東西看懂,您就真能 摘掉什么帽子? ”奶奶立刻不語,唯低頭盯著那張報紙,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動。我的心一下子收 緊,但知已無法彌補。“奶奶。”“奶奶!奶奶——"我記得她終于抬起頭時,眼里竟全是慚愧,毫無 對我的責備。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離開那張報紙,離開燈光,離開我,在窗上老海棠樹的影子 那兒停留一下,繼續離開,離開一切聲響甚至一切有形,飄進黑夜,飄過星光,飄向無可慰藉的迷 茫和空荒……而在我的夢里,我的祈禱中,老海棠樹也便隨之轟然飄去,跟隨著奶奶,陪伴著她, 圍攏著她;奶奶坐在滿樹的繁花中,滿地的里,復張望,或不斷地要我給她說說:“這一段到底是 什么意思? ”——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娘的手
娘的手,是一雙地地道道老農民的手,粗糙,黝黑,一到冬天就干裂的像棗樹皮,每個關節都 會裂開一道道深深的口子,順著裂開的口子流淌出來的血跡,干結在手面上,像一條條丑陋的娛蚣, 讓人不忍直視。為了緩解疼痛,每天晚上,娘都會用熱水燙很長,娘是個會過日子的人,舍不得浪 費一丁點的東西,哪怕是半盆水,也舍不得換掉,水涼了,就把盆放到火爐上,一邊加熱一邊燙。 這樣把手上干裂的一條條裂痕燙的軟了,再用?膠布粘起來,就不會影響第二天干活。
從記事起,娘的手就沒有閑下來過,也沒有好好的一天。每年的春雷還沒有敲響,娘早就
扛著 鍬頭把家里的山挨個細細的翻一遍,撒好肥料,只等著一場春雨的到來,就播下的種子。“春風裂 樹皮”,這句話在娘的手上體現的淋漓盡致,因為翻地的震蕩,一雙手上長長短短的裂痕比起冬天 有過之而無不及。原來冬天只是一個個關節處裂開,那么春天整個手面都會被密密麻麻的裂痕覆蓋 均勻。手指的關節處還好,可以用用膠布粘合,可是手面上卻只能任由一道道裂痕毫無忌憚的咧嘴 笑著。
在娘的手上,找不到一丁點手的溫潤和靈秀,可是娘的一雙手在十里八鄉是出了名的巧手。不 僅為一家老小納鞋底做鞋子,扯了布做衣服,還經常為鄰居家剛出生的小寶寶們,做貓頭鞋做連腳 褲。農民種地,免不了有些荊棘的刺會不留情面的深深的扎進手里,扎在表皮的還好,自己可以弄 出來,扎到肉里頭的,不只是疼得厲害,而且不敢碰鋤頭鍬頭,一碰鋤頭鍬頭的柄就會錐心的疼。 每隔幾日,就會有莊里相親毗牙咧嘴的來找娘,而娘總能靈巧的把別人的難題給輕松地解決掉。說 也奇怪,別人挑刺,都會疼,而且會出血,尤其是扎的深深的刺,可到了娘的手里,用一只手掐著, 另一只手拿個縫衣針,(有時候在坡里,直接用個荊棘刺),向左挑挑,向右挑挑,扎刺的人從不 說疼,還不會出血。被娘挑過刺的人,都為娘的“技術”一?次次的豎起大拇指。
不僅僅是挑刺,娘的勤快和熱心也是村里的人人人夸獎的。誰家有點大事小事,娘總會跑前跑 后的幫著張羅。誰家有個急事難事,娘總是傾盡全力的去幫助。通常,左鄰右舍,有蓋屋打墻的, 家里有病的,娘就會把做了的好吃的,還有家里的油啊,米啊,給人家送去。在那個吃不飽飯的年 代,娘常常自己餓著肚子,卻端了一碗飯送給鄰家。用娘的話說:“不就是自己少吃一口嗎,能幫 到人,就很好。”
有一年夏天,一個鄰居嫂嫂家的豬要下崽,碰巧腰疼的站不起來,娘提前好幾天,就幫著嫂嫂 觀察母豬的動靜。那個年代,農村人家里的母豬可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搖錢樹,一家老小的開銷就指 著它呢。終于在一個煙霞旖旎的傍晚,老母豬鼓鼓的肚子蠢蠢欲動了,娘和嫂子蹲在豬圈里,一會 兒給豬喂點水,一會又給它輕輕地揉揉肚子,一刻也不敢,直到晚上十點多,才誕下了第一個豬仔, 娘和嫂子,一邊幫著接生,一邊給生下來的幼崽擦洗身上的羊水和血跡之類的臟東西。雖然不是自 家的豬下崽,可是娘和嫂子一樣,到凌晨一點多,那只老母豬一共誕下了十三只幼崽,這下把娘和 嫂子都樂壞了。正在她們開心時,突然有一只幼崽出現了意外,渾身哆嗦奄奄一息,按說,夏天 的晚上,熱的人喘不過氣來,豬的幼崽不應該哆嗦才對,娘緊張的把幼崽抱在懷里,用自己的體著 幼崽,又讓嫂子去拿來一片土霉素壓碎了,用溫水沖開,給幼崽喂了下去。因為擔心別的幼崽也會 這樣,娘和
嫂子,挨個喂了一邊土霉素水。整整折騰了一夜,出現意外的幼崽才恢復正常。娘踏著 黎明的曙光,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時,滿身的豬圈味和一雙骯臟的手把我逗得開心的跑開了。
記得上初中那會兒,幾輩莊稼人盼著石頭能賣錢的夢終于圓了。累彎了i代又一代莊稼人的大 山終于有了用途。有個遠處的大老板,看中了我們臨近兒個村的山石,和村里簽了合同,常年購買 我們這兒的石頭。當各村大喇叭一廣播這好消息,村里沸騰了,祖祖輩輩為之發愁的大山,終于可 以換銀子花了,終于可以讓村民們發家致富了。
從那天開始,沉寂多年的山活躍了,貧瘠的山頭,時不時的傳來一聲聲放炮的聲音,驚天動地 的炮聲和刺鼻的炸藥味,給村民們敲響了新的樂章。娘的手更忙碌了。每天天不亮,就去自家地里 打理莊家,吃了早飯,就扛了鐵錘爬一公里的山路去石材廠砸石頭,被炸藥炸裂的石頭,大大小小 的躺在采石場。娘和村里的七姑八姨們一起,幾個人一組,再把那些大小不一的石頭敲成均勻的小 石子,敲完以后裝到拖拉機上,拖拉機再一路顛簸的運到盛放石子的貨臺上。
當拉著長笛的火車駛進鄰村小站時,娘和鄰居們就挑著筐,拿著鍬和五個齒的金叉頭一路
小跑去 車站貨臺,把事先用拖拉機拉來的石子沿著走起來顫巍巍的架板,挑到車皮里,一擔一擔的把容量 兩三噸的車皮喂飽填滿。火車好像知道村民們對它無比的,總是任性的不分早晚。有時候下著瓢潑 大雨,有時候剛下完雪,或者干脆有時候就在人們睡的正濃的午夜,可是村民們對它太寵溺了,不 管它在何時來,都能精神抖擻的拿起家什,頂著風,冒著雨,披著滿天星光,烤著蒸蒸烈日,一路 喊著路過的鄰居的名字,有說有笑的投入到一身泥一身汗的繁重搬運中。
那時候,因為砸石頭,娘的手上一到秋天就會橫七豎八的沾滿膠布,疼痛自是不必說,每逢在 家攤煎餅,更是難熬。常常見到娘,在折疊剛剛熟的煎餅時,折好一個煎餅,就皺著眉頭把手放到 嘴邊吹一吹,緩解疼痛。盡管如此,可是娘卻從來沒有因為手疼而一天不去砸石頭,也沒有因為手 疼而裝一次車皮,更沒有因為手疼,讓那一頓飯缺了炊煙。娘經常一只手里拿著卷根咸菜的煎餅一 只手里拿著家什去地里干活,風里來雨里去,忙完玉米地再去紅薯地。
直到現在,我依然無法想象娘那雙在凜冽的寒風中流淌著斑斑血跡的雙手是如何的疼痛,娘是 用怎樣的一錘又一錘的敲打著那些堅硬的石頭,娘又是用怎樣的毅力砸了那么多年的
石頭。那時候, 娘的手上起滿了老繭,長期的手工勞作,把手掌的紋理都磨平了,每次摸娘的手,都像被搓搓到了 一樣,撓的手只癢癢。
現在,娘的一雙兒女都成家了,娘也跟著都住進了城里,住上了樓房。按說,娘應該享享清福 了,可是娘依然閑不住,經常樓上樓下的幫著收水費呀,打掃樓梯呀,擦個樓道玻璃呀,整個樓棟 的人,都說自從娘來了,鄰居之間的話多了,也和睦了,不像以前那樣樓上樓下的不認識,見面只 是點個頭。娘不僅僅是維護公共衛生的,更是增進鄰居的大使。娘也會經常抽個弟弟弟妹的假期, 不用帶,跑回老家,把房前屋后打掃得干干凈凈,把成片的香椿樹,梧桐樹地修理的沒有一顆雜草。
一年一年,山,還依舊那樣年輕,黑土地,還是一年一年的綠了又黃了,娘,卻一年比一年老 了。鬢角留下了歲月的霜白,額頭刻下了年輪的影子,可是娘的手,卻還是年輕時的樣子,雖粗糙 卻不笨拙。娘也還是年輕時的樣子,誰家有個紅白喜事,誰家有片愁云慘霧,娘依然不減當年樂于 助人的熱情,用不再那么穩健的腳步,忙于東鄰西舍家,用那雙依然勤勞的手,編制著的生活。
后母的三巴掌
從六歲至今,跟后母一起生活了 30年,烙在我骨血里磨不掉的是后母印在我屁股上的三巴掌。
第一巴掌是我8歲那年夏天,我同伙伴從賣甜瓜的老頭兒筐里偷了一只甜瓜,跑回家躲在街門 后頭吃。
“哪來的? ”后母看出不對勁兒了。
“偷的。”我還覺得挺得意,挺能耐。
“啪! ”后母二話沒說,把我拽過去照準屁股就是一巴掌,又響又干脆。疼得我腿肚兒直轉筋, 咧開嘴半天沒哭出音來。
“做賊!與老鼠一個祖宗!恨死人!把瓜扔了!不許吃!給,給老頭兒送錢去! ”后母那嚴酷 的表情是我從沒見過的,我怕極了,不敢哭,接過兩毛錢扔了瓜咧著嘴給賣瓜的送錢去。從此,別 人多稀罕的東西都沒動過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