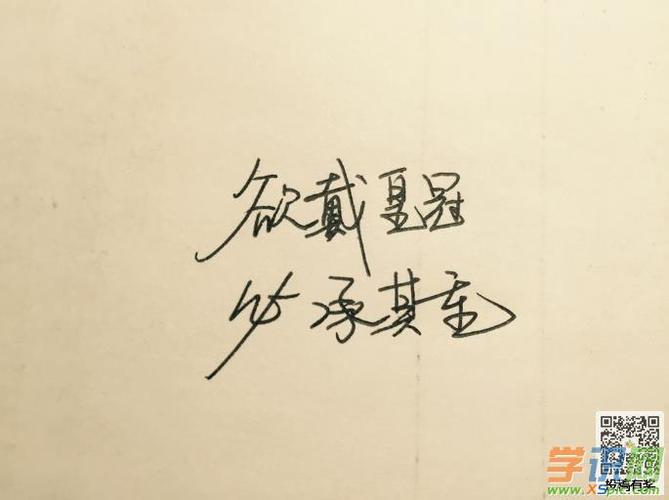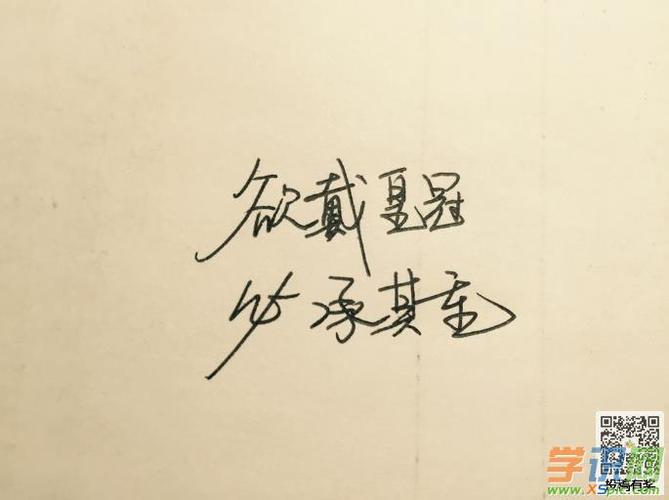
禪宗與精神分析
我們所討論的禪宗與精神分析這兩個體系,都是關于人之本性的理論,又是導致人之幸福的實踐。兩者都分別是東方和西方思想的獨特表現。禪宗是印度理性與抽象性同中國的具體性與現實主義相融合的產物。如同樣屬于東方一樣,精神分析完全是西方的產物:它是西方人道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產物,也是19世紀對理性主義所把握不住的隱秘力量進行浪漫主義式探究的產物。再往前追溯,希臘智慧和希伯來倫理,則為這門科學療法的精神之父。
盡管精神分析與禪都討論人的本性及導致人轉變的實踐,但它們的區別看來超過其相似之處。精神分析是一種科學,完全是非宗教性的;禪則是一種達到開悟的理論與方法,一種在西方人看來可說是宗教性或神秘性的體驗。精神分析是對精神疾病的一種治療方法,禪則是一條精神拯救之路。那么,對精神分析與禪宗關系的討論,其結論是否就只能是這兩者間除了不可逾越的鴻溝外不存在任何關系呢?
然而卻有許多精神分析學家對禪產生了與日俱增的興趣。這種興趣的根源何在?其意義又是什么?本文試圖對此作一回答,但并不企圖對禪宗思想作系統描述,這一任務超出了我的知識與經驗;我也無意對精神分析作全盤介紹,那將超出本文的篇幅。不過,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將略費筆墨,介紹與禪宗關系密切的精神分析中的若干重點。這些重點代表了從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延伸出來的基本概念,這有時被我稱作“人道主義的精神分析”。我希望以此表明,研究禪宗為什么對我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并且相信,這對所有精神分析的研究者都不無神益。
一、當今精神危機與精神分析的作用
在展開這一課題之始,我們必須反省在這生死存亡的歷史時期,西方人在精神上所經歷的危機,以及精神分析在這一危機中所起的作用。
雖然大部分西方人沒有自覺地感受到(可能大多數人永遠不會站在激烈批判的立場上意識到這一危機)他們正經歷著西方文化的危機,但至少有一部分持批判態度的觀察者已承認這一危機的存在,并了解它的性質。這一危機可描述為諸如:“不安”,“厭倦”,“時代病”,“麻木不仁”,人的機械化,人與自己、與他的同胞。與自然界異化。人追逐理性主義,已到了使理性主義變得完全非理性的地步。從笛卡爾以來,人就日益將思想與情感分離;人們認為只有思想才是合理的,而情感本質上即是非理性的。人被劈成兩半,一半是知性,這被認為是真正的我(1),它要支配另一個我(me),如同支配自然一樣。用知性去支配自然及所生產的越來越多的物品,成為生活的最高目標。在這一過程中,人把自己變成了物,生命變為財物的附屬,存在(to be)被占有(to have)所支配。在西方文化的源頭--無論是希臘還是希伯來,生活的目標是追求人的完美;而在現代人這里則是追求物的完美,以及如何創造它們的知識。西方人現在處于一種不能體驗情感的人格分裂狀態,因而感到焦慮、抑郁和絕望。口頭上他仍把幸福、個人主義和首創精神視作生活的目標,但事實上他并沒有目標。若問他為什么活著,他這一切奮斗到底是為什么,他會感到困惑。有人會說是為了家庭而活,有人會說是為了“玩樂”而活,另外一些人則會說是為了賺錢而活,但在實際上,沒有誰知
道為什么而活;除了想逃避不安全感與孤寂感之外,他沒有任何目標可言。
的確,今日進教堂的人比以往更多,宗教書籍亦頗為暢銷,人們比以往更多地談到上帝。但這種宗教現象只是掩蓋著深處的物質主義態度和非宗教的態度,這種現象可理解為對19世紀傾向(以尼采“上帝死了”的名言為特征)在意識形態上的一種反動,這種反動導因于人們的不安全感和認同感。實質上,在這種現象里找不到真正的宗教態度。
從某個角度看來,19世紀對有神論觀念的拋棄,是件不小的成就。人們向現實邁出了一大步。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在一切被創造物中,人喪失了由上帝所指定的支配其他被造物的中心角色。從新的客觀現實來研究人的潛藏動機,弗洛伊德認為對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信仰,乃植根于人類生存中的無助狀態。人為了克服這種狀態,便只能信仰以上帝為象征的父母和他們的幫助。他認為,人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偉大導師的教導,父母、朋友和愛人洋溢著愛的幫助雖能幫助他,也不過是幫助他勇敢地接受生存的挑戰,并全力以赴地回應這一挑戰。
人放棄了如父母般伸出援助之手的上帝的幻象,但他同時也放棄了一切偉大的人道主義宗教的真正目標:克服一己之我的局限,達到愛、客觀(objectivity)、謙和,尊重生活從而使生活本身成為生活的目的,使人成為其潛能得以實現的人。這些既是西方各大宗教的目標,也是東方各大宗教的目標。但是,東方沒有超驗的天父-救主這種觀念的負擔,而西方的一神教卻對這一超驗的觀念表示強烈的向往。
道教和佛教在合乎理性與現實主義方面,優越于西方宗教。他們能夠如實地、客觀地看待人,因為沒有別人,只有“覺者”才能作人的導師;而人們之所以能被他們引導,乃在于人入內心里皆有覺醒與開悟的能力。東方的宗教思想--道教與佛教,以及兩者的結晶禪宗,所以對當今西方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原因即在于此。禪宗幫助人們為其生存問題尋找答案,這個答案本質上同猶太教一基督教的傳統答案并無二致;但禪宗的答案卻不違背理性、現實主義與自主性,這正是現代人的極其可貴的成就。東方的宗教思想比西方的宗教思想更合乎西方的理性思想,這的確是耐人尋味的悖論。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概念中的價值與目標
精神分析典型地表現了西方人的精神危機以及謀求解決這一危機的意圖。在精神分析學說的最新發展中,在“人道主義”的或“存在主義”的分析中,明顯地呈現出這一趨勢。但在討論我自己的“人道主義的”概念之前,我要說明的是,與大多數人所認為的完全相反,弗洛伊德本人的體系超出了“疾病”與“治療”的概念,關系到人的“拯救”,而不僅僅是對精神病人的治療。從表面上看,弗洛伊德是新精神病療法的創始者,他的主要興趣和畢生為之努力的主題也在于此。但是,若進一步觀察,我們可看出在對神經癥進行治療的醫療觀念背后,有著一種完全不同的興趣,這種興趣弗洛伊德很少表明,很可能連他自己都未曾意識到。這一隱藏的思想并不涉及精神疾病的治療,而是涉及一種超出疾病與治療觀念的東西。這種東西是什么呢?他所發起的“精神分析運動”的性質是什么呢?弗洛伊德對人類未來的看法是什么呢?他的運動賴以建立起來的教條又是什么呢?
弗洛伊德對上述問題最明確的答案可能是:“哪里有本我(id),哪里就得有自我(Ego)。”他的目標在于用理性控制非理性的、無意識的欲望,在于使人從他的無意識力量中解放出來。人想控制自己的無意識力量,就必須對之有所認識。他的目標是對真實有恰如其分的知識,這種知識乃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的指路明燈。這些目標是理性主義、啟蒙哲學與清教倫理的傳統目標。不過,當宗教與哲學以一種可以稱之為“烏托邦”的方式提出了這些自我控制的目標后,弗洛伊德卻是(或自己相信自己是)第一個通過無意識的探測把這些目標建立在科學
的基礎上,并指出如何實現這些目標的人。弗洛伊德代表了西方理性主義的頂點,與此同時,他又以他的天才克服了其中虛假的理性主義與膚淺的樂觀主義方面,創造性地把理性主義與浪漫主義結合起來。而19世紀的浪漫主義運動,以其對人的情感的非理性方面的熱衷和崇尚,本來是與理性主義相對立的。
至于對個人的治療,弗洛伊德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為關心哲學與倫理上的目標。在《精神分析引論》中,他談到某些神秘實踐用來導致人格根本轉變的種種嘗試。他接著指出:“我們不得不承認,精神分析的治療結果亦選擇了類似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加強自我(EgO),使其日益從超我(Super-Ego)中獨立出來,擴充其視野,以便從本我(Id)中奪取更多的地盤。哪里有本我,哪里就得有自我。這是一種像開拓須德海②一樣的文化工作”。他又以同樣的口吻說道,精神分析療法意在“把人從神經癥癥候、壓抑及變態性格中解放出來”。他也同樣看到,精神分析者的作用并不限于作一個“治病”的醫生。
他說:“精神分析者必須在某種意義上處于超然的地位:在有些分析情境中,他是患者的楷模;在另一些情境中,他得做患者的教師。”他又寫道:“‘最后,我們不可忘了,分析者與患者的關系,建立在對真理的愛上面,即建立在對現實的認知上,它排除任何形式的虛偽與欺騙。”
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概念中,還有一些超越通常疾病與治療概念的因素。熟悉東方思想--特別是禪宗--的人,將會注意到下述因素與東方思想中的概念并非無關。首先要指出的是弗洛伊德關于知識導致轉變的概念,他認為理論與實踐密不可分,在認識自己這個行為中,我們也就改變了自己。毋庸贅言,這一觀念同弗洛伊德當時和我們這一時代科學心理學的概念有多大的不同,在這種科學心理學中,知識本身僅停留在理論上,對知者卻沒有轉變的作用。
弗洛伊德的方法還有一點與東方思想(特別是禪宗)密切相關。弗洛伊德并不贊同給有意識的思想體系以高度評價,而這恰恰是現代西方人的典型態度。相反,他認為我們有意識的思想只不過是我們整個精神過程中的一小部分,同淵源于內心深處的巨大力量相比,實在微不足道;這種力量是隱秘的、非理性的,同時又是無意識的。為達到對人的真正本性的洞察,弗洛伊德用自由聯銀的方法,打破有意識的思想體系。自由聯想繞開邏輯的、有意識的、通常的思維方式,它把我們導向人格的新淵源,即無意識領域。不管對弗洛伊德無意識領域的內容有什么樣的批評,事實上他已因強調自由聯想方法,而超越了西方通常的理性思維模式這一基點,從而轉入新的趨向,這在東方思想中已有更徹底更長足的發展。
還有一點是弗洛伊德與當代西方態度完全不同的。這里指的是,他愿花費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或更多時間為同一個人做精神分析。這種療程事實上使弗洛伊德受到諸多非議。毋須多說,我們應當力求使精神分析盡可能迅速有效;但我在這里要強調的是,弗洛伊德有勇氣說為一個人花費窮年累月的時間是有意義的,只要這種努力能幫助他了解自己。從功利觀點、盈虧的角度來看,這樣做是不值得的。人們會說,從社會效果上看,為了一個人的轉變花費這么多的時間去做這樣一種冗長的分析,是不值得的。要理解弗洛伊德的方法,只有超越現代的“價值”觀念,超越手段與目的之間的關系的現行觀念,超越收支平衡表。如果我們認為一個人不可與任何物相比擬,如果他的解放、他的安寧、他的覺悟--無論我們愿意使用什么樣的說法--乃是我們的“終極關懷”本身,那么我們就不能用時間和金錢來量度這一目的。提出這樣一種寓含著對一個人巨大關切的方法,是具備著遠見卓識和勇氣的,尤為重要的是,它所體現的態度超越了西方的傳統思想。
上述評論,并不意味著弗洛伊德已自覺地接近東方思想,尤其是禪宗思想。前面提及的許多因素,在弗洛伊德心中,與其說是有意識的,倒不如說是無意識的。弗洛伊德完全是西方文化、尤其是18--19世紀思想的產兒,他不可能接近禪宗中表現出來的東方思想,即使他熟悉這種思想也是徒然。弗洛伊德對人的描寫,本質上是18一19世紀的經濟學家與哲學家所描繪的圖像。他們把人根本上看作是競爭的、孤立的,與別人的聯系僅僅出于交換上的
需要,滿足經濟與本能的要求。在弗洛伊德看來,人是一個受力比多驅使的機器,由將力比多興奮保
持在最低限度的原則控制。他認為人基本上是利己的,只是為了滿足本能欲望的需要,才各自與他人發生關系。在弗洛伊德看來,快樂是對緊張的松弛,而不是對喜悅的體驗;人被看成知性與情意截然割裂;人不是完整的人,而是啟蒙哲學家所說的知性自我;友愛是一種與事實背離的不合理要求;神秘體驗是一種向嬰兒期自戀的退化。
我所力圖說明的是,弗洛伊德的體系中雖有這些同禪宗明顯相違之處,卻仍然有一些因素超越了通常的疾病與治療的觀念,超越了關于意識的傳統理性觀念,這些因素導致精神分析進一步的發展,這一發展與禪宗思想有著更為直接和肯定的聯系。
不過,在討論“人道主義的”精神分析與禪宗的聯系之前,我想指出對理解精神分析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的一項變化,即要求進行分析的患者及他們所提出的問題發生了變化。
在本世紀初,來找精神病學家的主要是患有病癥的人。他們或者是一只手震顫癱瘓,或者是有強迫性的清洗痛,或者為某些強迫性的念頭所折磨。換言之,按照“病”這個字在醫學上的意義,他們是生病了;某種東西妨礙了他們不能像所謂正常人一樣行使其社會功能。如果這就是他們患病的原因,那么他們的治療概念是與疾病概念相應的。他們想排除這些病癥,他們的“健康”觀念就是--不要生病。他們要求與常人一樣健康,或許可以這樣說,他們不想比社會上通常的人更不快樂、更不安寧。
這些人現在仍求助于精神分析家,精神分析對他們仍是一種排除病癥、發揮其社會功能的治療方法。
不過,他們以前在精神分析家的病人中占多數,現在卻成了少數--或許這并非因為他們在絕對數量上的減少,而是與許多新‘編人”比較,在比例上成了少數。今天的這些新“病人”能發揮正常的社會功能,并非通常意義上的病人,但他們確實患著“時代病”,即我前面所說的那種壓抑和麻木不仁。精神分析家的這些新“病人”,并不知道他們患的是什么病。他們抱怨著內心沮喪、失眠、婚姻不幸福、工作無趣味,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煩惱。他們通常相信,這種或那種特定癥狀即是癥結所在,只要排除這些癥狀,就會一切如常。但他們通常未曾看到,他們的問題不在于沮喪、失眠,以及他們的婚姻或工作。這種種抱怨只是我們的文化允許他們表達內心深處某種東西的自覺形式,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有著所有自以為患著這種那種特定病癥的人所共有的疾病。這個共同的疾病,即人同人自己、同他的同胞、同自然的疏離,是感覺到生命像砂子一樣從手中流失,還未懂得生活就將死去;是雖生活在富裕之中卻無歡樂可言。
精神分析能對這些“時代病”患者提供什么幫助呢?這個幫助是--而且必須是--不同于以往那種排除癥狀、使患者重新發揮其社會功能的“治療”的。對于那些在異化中受苦的人,治療并不在于使他免除疾病,而在于使他獲得幸福安寧(well-being)。
然而,對幸福安寧下定義,卻是相當困難的事。如仍停留在弗洛伊德體系中,則幸福安寧就不得不用力比多理論來界定,這不過是能夠充分發揮其性功能而已;或者換一個角度,是對隱藏的俄狄浦斯情結的察覺。這些定義在我看來,只觸及真正的人類存在問題及完整的人所達到的幸福安寧的邊緣。任
何對幸福安寧的嘗試性回答,必須超越弗人類存在的基本概念乃是人道主義精神分析的基礎。只有這樣,才能為比較精神分析與禪宗思想奠定基礎。
三、幸福安寧的性質--人的精神進化
界定幸福安寧,第一步可作如下表述:幸福安寧是與人的本性相一致的存在狀態。若再深入一步,我們會提出過詳的問題.就人的生存條件而言,這存在狀態究竟是什么?這些條件又是什么?
人的生存蘊含著這樣一個問題:他不由自主地被拋入這個世界,又不由自主地被帶離這個世界。動物天生就稟賦著適應環境的機制,它完全生活于自然之中;與動物相比,人缺乏這種本能機制。他不得不主動去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左右。他身處自然之中,卻又超越了自然;他能意識到自己,但意識到自己是個分離的存在物又使他感到無法忍受的孤獨、失落與無能為力。出生這一事實本身就蘊含著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從他誕生那一刻起,生活就向他提出了問題,這一問題必須由他回答。每時每刻,他都必須回答它;不是用他的頭腦,也不是用他的軀體,而是用他的全部身心來回答,用那會思、會夢、會睡、會吃、會哭、會笑的他來回答。生命所蘊含的這個難題到底是什么?這就是:我們如何克服困隔離感而產生的痛苦、禁錮和羞愧?如何才能與我們自己、與我們的同胞、與自然合為一體?人不得不以各種方式回答這個問題;即便是瘋狂,也是一種解答。通過瘋狂而擺脫外在世界,完全把自己封閉在自我的殼中,這樣便能克服隔離的恐懼。
問題永遠是相同的,答案卻五花八門。不過根本上只有兩種答案。一種是以退化到知覺尚未產生的合一狀態--人誕生前的狀態--來克服隔離。另一種答案則是完全的誕生,是發展人的認知、理性及愛的能力,達到一種超越自我中心的境地,從而與世界達成新的和諧、新的統一。
我們說的誕生,通常指生理上的分娩,這是十月懷胎后的結果。但這種誕生的重要性在許多方面都被過高估計了。重要的是,嬰兒在初生頭一周,同成年男女相比,更像是處于子宮之中。不過,誕生卻有一個獨特的方面:臍帶被剪斷了,嬰兒開始了它的第一個活動--呼吸。從此以后,割斷每一條原始紐帶,都只有靠真正的活動才能實現。
誕生不只是一個行動,而是一個過程。生命的目標在于完全誕生,可悲劇卻在于我們中的大多數人至死都沒有達到這種誕生。活著就是每一分鐘都在誕生。一旦誕生停止,死亡也就來臨。從生理學上看,我們的細胞組織處于不斷誕生的過程中;但從心理學上看,我們大多數人卻在到達某一點后就不再誕生。有些人完全就是死胎,在生理上他們繼續活著,在心理上卻渴望返回到子宮、大地、黑暗和死亡;他們是瘋狂者或接近發瘋者。另有許多人在他們的生命的道路上繼續推進,但他們依然不能把臍帶完全剪斷;他們對母親、父親、家庭、種族、國家、地位、金錢、神祗等仍有著共生性的依附;他們從未完全成為他們自己,從而也就從未完全誕生。
對生存問題企圖作退化性的解答,可以采取各種不同的形式;但這些人的共同點則在于他們注定失敗,
并導致痛苦。人一旦從與自然處于前人類的、樂園式的合一狀態中分離;他就決不能返回他所從出的狀態,兩個帶著火劍的天使阻擋了他的退路。只有死亡或瘋狂--而不是生活與清醒--才能達到這種復歸。
人可以在幾個層面上尋求這種退化性的結合,但這同時也是病態的與非理性的層面。他可能被返回子宮、返回母親大地、返回死亡的渴望所主宰。如果這個目標是耗盡一切而無限制的,其結果就是自殺或病狂。另一種尋求合一的退化方式較少危險,也較少病態,它的目的是與母親的懷抱、或母親的手、或父親的命令連結在一起、各種目的的差異,表示著各種人格的差異。那些想留在母親懷抱中的人,是永久依賴性的乳兒,當他被愛、被照顧、被保護、被贊美時,他會有一種安適感;當他遭受同充滿慈愛的母親分離的威脅時,他就充滿不可忍受的焦慮。同父親命令連結在一起的人,也許會發展出相當大的主動性與活動性,但他永遠都匍伏在一個對他發號施令、獎賞或懲罰他的權威腳下。另一類退化傾向蘊于破壞性中,旨在以破壞一切人和物的欲望來克服隔離。他可能是以吞食一切人和物的愿望尋求這一點,就是說想把世界及萬物都當作口中之食,或除了自己外要完全毀滅一切。另一種企圖克服隔離痛苦的方式,在于建立人們的自我,成為一個隔離的、確定的、不可破壞的“物”。于是,他把自己感受為他的財產、他的力量、他的聲望和他的智力。
一個人要想從他的退化性結合中擺脫,必須逐漸克服他的自戀傾向。就初生兒來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