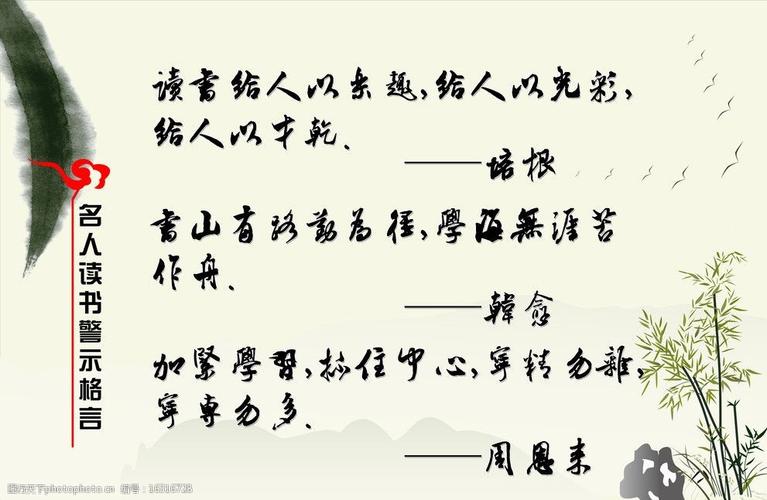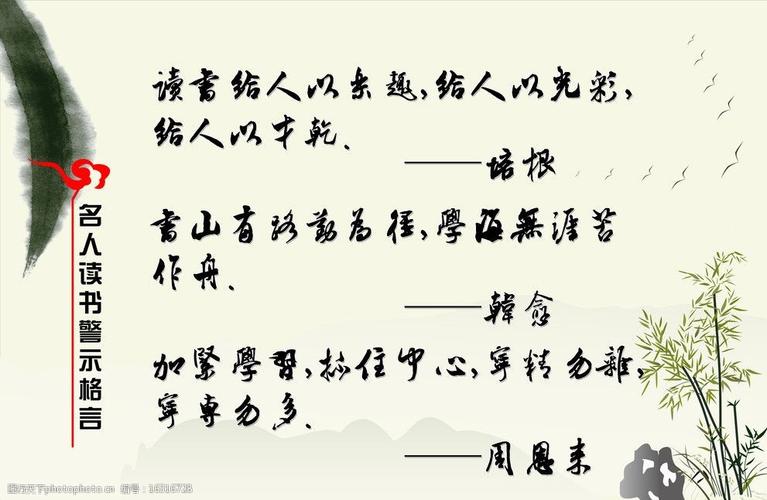
56
試論蘇軾詞中的《莊子》思想
文/鄧琳
摘要:蘇軾一生出入儒、釋、道,集三者于一身,擷取各家精華以鑄成蘇學,由他詞作中流露出的樂天達觀、逍遙自適的人生態度,尤可見出蘇軾忘懷一切得喪禍福而與造物者神游的審美化精神境界。蘇軾將《莊子》一書的精神內涵內化為自己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不僅對他的人生境界產生深遠影響,還進而使蘇軾成為超曠人生境界的文人典范。
關鍵詞:逍遙;物化;莊子;蘇軾前人對于蘇軾的莊學思想研究和蘇詞的研究都可謂是著述宏富,但在對蘇軾莊學思想進行論述時幾乎都是引用他的詩文集或書信、策論,很少引他的詞作為莊學思想的證明,在論述詞中的哲學思想時又往往雜糅儒、釋泛泛而論,很少有只針對莊學思想進行研究的。這或許是與長久以來“詩莊詞媚”的認識有關,但正是詞這種文學體裁的特殊性使它可以更自由、真實地表達情感,從而可以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蘇軾對于莊學思想的吸收和超越,從對《莊子》典故的運用、對莊子逍遙物化精神的內化看出蘇軾的思想軌跡,進而對他的宇宙觀、窮達觀、處世觀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一、蘇詞中的莊學精神
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曾提到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①蘇軾不僅是一位文學家,還是一位思想家,他的莊學思想除可見于《廣成子解》,亦流露于他的詩詞文中。更重要的是蘇軾將《莊
子》一書的精神內涵內化為自己的人生態度和處世哲學,蘇軾自踏上仕途后總是多災多難,逆境多于順境,“一生凡九遷”,但他總能以樂天達觀、逍遙自適的人生態度來面對,不可不謂是受到《莊子》的極大影響。如他所謂“觀魚并記老莊周”(《壽州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逍遙齊物追莊周”(《送文與可出守陵州》)“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醉白堂記》)等等,無不說明他在坎坷艱難的人生經歷后與莊子的“齊物”“逍遙”思想發生共鳴,從而每每進入一種忘懷一切得喪禍福而與造物者游的審美化精神境界。這種逍遙齊物的思想對蘇軾的人生境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進而使蘇軾成為超曠人生境界的文人典范。
(一)夢蝶乘鵬學莊周——游于物外的宇宙觀
<;在宥>中說“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在消除了主觀偏見、個人妄念后,就會消除人為造成的物我之間的界限,從而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忘我境界,這種物我合一后獲得精神自由的莊學思想不僅成為蘇軾的哲學觀念,還流露
于他的詞作中,最直觀的體現在于蘇軾對《莊子》中典故的化用。
如在《南歌子·再用前韻》一詞中化用莊周夢蝶的典故:
帶酒沖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鐘鼓報天明。夢里栩然蝴蝶、一身輕。
老去才都盡,歸來計未成。求田問舍笑豪英。自愛湖邊沙路、免泥行。
此作是詞人冒雨趕路后帶著醉意與疲態和衣睡去,化蝶夢醒后所作,“夢里栩然蝴蝶、一身輕。”一句化用<;齊物論>“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可以理解為詞人借以表達冒雨趕路酣睡醒來的輕松自足之態。由此詞作于謫居黃州時期的背景,下闕“求田問舍笑豪英”言自己胸無大志,不再系心于政務世事之意,也可合理推測詞人在借莊周夢蝶表達自己寄情山水田間的放達心境和物我兩忘的逍遙之態,觀莊周夢為蝴蝶后“自喻適志”的適心暢志與蘇軾“一身輕”的自快之貌,足可見蘇軾與莊子相通的心志。
又如《鵲橋仙·七夕和蘇堅韻》
乘槎歸去,成都何在,萬里江沱漢漾。與君各賦一篇詩,留織女、鴛鴦機上。
還將舊曲,重賡新韻,須信吾儕天放。人生何處不兒嬉,看乞巧、朱樓彩舫。
“天放”取語于《莊子·馬蹄》:“一而不黨,命曰天放。”郭象注“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②,成玄英疏“天,自然也。……若有心治物,則乖彼天然,直置放任,則物皆自足,故名曰天放也。”③詞人言自然任物以自足來寬慰友人并非毫無來由,時值乞巧佳節,詞人出京補外,遠離故土,又難展濟世之志,便與友人相約唱和解憂,“須信吾儕天放”,不再刻意治物,轉而順物自然,由此便可得物之自然,正是詞人不汲汲于物,曠達個性的真實展現。
再如《念奴嬌·中秋》
憑高眺遠,見長空萬里,云無留跡。桂魄飛來,光射處,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瓊樓,乘鸞來去,人在清涼國。江山如畫,望中煙樹歷歷。
我醉拍手狂歌,舉杯邀月,對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風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水晶宮里,一聲吹斷橫笛。
月光冷浸,滿天碧透,月宮仙人乘鸞飛行,詞人邀酒明月的狂態與醉態使得騎鵬歸月顯得超然而又自然。“騎鵬翼”一句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逍遙游>中“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鵬,然而此時詞人已無需借助鵬鳥,意飛天外,身已置于水晶宮中與仙人共游。雖身困黃州,“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