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8日發(作者:非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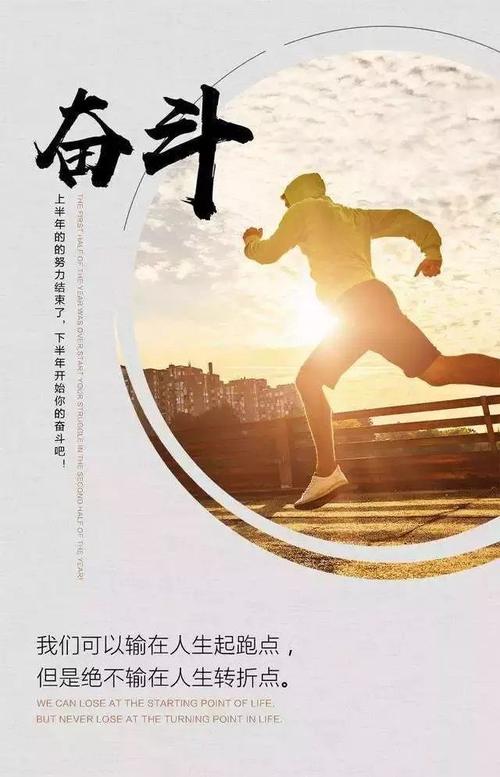
元豐元年,蘇東坡為紀念戰勝洪水的壯舉,在徐州城東門之上建造大樓,并邀請文人雅士飲酒作賦,以示慶賀。高郵人秦少游派專人呈上一份高郵土特產,并附詩一首:
“鮮鯽經年漬醽醁,團臍紫蟹脂填腹。后春莼茁滑于酥,先社姜芽肥勝肉。鳧卵累累何足道,饤饾盤飧亦時欲。淮南風俗事瓶罌,方法相傳我旨蓄。魚鱐蜃醢薦籩豆,山蔌溪毛例蒙錄。輒送行庖當擊鮮,澤居備禮無麋鹿。”
這首名為《以莼姜法魚糟蟹寄子瞻》是秦少游少有的專寫食物的詩,但這首詩卻濃縮了高郵最具特點的美食。有了秦少游作為先例,高郵的文人便多少都對美食有了那么一點癖好。于是,在900年后的高郵,就又出了那么一個“文人食客”,那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與故鄉的美食
汪曾祺的嗜吃,在現代文學史上可謂是出了名的,金庸就曾說過,大陸“滿口噙香中國味的作家,當推汪曾祺和鄧友梅。”汪老的癖好之所以如此聞名于天下,更重要的不僅在于他會吃,更在于他會寫吃。你看,汪老留下的散文與散文集自然是浩如煙海,其覆蓋的主題之廣自然不用多說,但要說汪老的文章涉及最多的、寫得最好的恐怕還當數“美食”。
不用說《汪曾祺談吃》、《吃食和文學》、《四方飲食》、《故鄉的食物》這一類直接在題目里凸顯“吃”這一主題的文章和文集,今年出版的“作家與故鄉”系列中汪老的兩本選集(《水蛇腰》和《我的高郵》)里依然能常常看到美食的“影子”。
對于汪老來說,天下美食派系眾多,“南甜北咸東辣西酸”(汪曾祺語)各地口味各具特色,但其中令汪老最難忘懷的,恐怕仍要數故鄉高郵的那些美食。汪老曾特意作《故鄉的食物》和《故鄉的野菜》等文給故鄉美食“作傳”,即是為證。
談到高郵的特產,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紅心咸鴨蛋。對于名滿天下的高郵鴨蛋,汪老自然不會忘掉,在《故鄉的食物》中被拿來單獨“立傳”也就不足為奇了。在汪老心中,高郵鴨蛋是故鄉的小食之王恐非夸大。在《端午的鴨蛋》一文中,汪老寫道,“高郵的咸鴨蛋,確實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鴨蛋多矣,但和我家鄉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咸鴨蛋,我實在瞧不上!”如此直白的語言,盡管一邊說對于異鄉人的稱道有著不高興,可是一邊心里的那種自豪卻是顯露無遺了。怪不得,即使是皇城根下產出的咸鴨蛋,在汪老眼里也只能被評價為“這叫什么咸鴨蛋呢!”。
高郵鴨蛋的妙處固然在于其美味,而“咸菜茨菇湯”對于汪老來說,吃得則就完全是一種情懷了。汪老在文中自陳,“我小時候對茨菇實在沒有好感,這東西有一種苦味。”然而,當汪老在老師沈從文家里,吃到師母張兆和做的“茨菇肉片”時,卻嘆道“因為久違,我對茨菇有了感情……我見到,必要買一點回來加肉炒了。”這道“茨菇肉片”,我小時候也常吃,長大以后卻很少見到。盡管有著較高的營養價值,但
大小飯館里卻極少見到拿其入菜的,再加上畢業后同樣地“背井離鄉”,因此我在讀此文時,對汪老的這種情感甚有共鳴。
汪曾祺的“美食觀”
當然,作為一個大作家,尤其是吃遍了大江南北美食的作家,汪老自然不會抱守著“故鄉的美食”不放。正如汪老自己所說,“一個人的口味要寬一點、雜一點。‘南甜北咸東辣西酸’,都去嘗嘗”(《四方食事》),在汪老眼里,只有這樣的“寬容精神”才能當好一個“美食家”。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汪老的口味崇尚“雜博”,但無論是日常菜饌,還是野味珍饈,在汪老的筆下總是透著一種美感。這大抵是因為,汪老的“吃”中自始至終透著一種五柳先生的散淡。汪老在《水蛇腰·故鄉人》里寫了一位“釣魚的醫生”,就頗能代表他所保持的那種“吃的哲學”:
“你大概沒有見過這樣釣魚的。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著。隨身帶著一個白泥小炭爐子,一口小鍋,提盒里蔥姜作料俱全,還有一瓶酒。他釣魚很有經驗。釣竿很短,魚線也不長,而且不用漂子,就這樣把釣線甩在水里,看到線頭動了,提起來就是一條。都是三四寸長的鯽魚……釣上來一條,刮刮鱗洗凈了,就手就放到鍋里。不大一會,魚就熟了。他就一邊吃魚,一邊喝酒,一邊甩鉤再釣。這種出水就烹制的魚味美無比,叫做‘起水鮮’。”
讀完這段文字,我想每個讀者恐怕都對“吃客”二字有了更深的認識。這種圖像恐怕不僅僅是投影了汪老的回憶,更是體現了汪老對待美食的一種態度。這種態度的傳承上可以企及魏晉,近則可追溯到晚明直至民國。
汪曾祺的文章與美食
談到這里,我們就要談談汪老的“文風繼承”了。盡管是西南聯大的科班出身,但由于幼年時期就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汪老的文章里帶有明顯的“士人遺風”。再加上長久傾心于宋人筆記和明清小品,汪老的文章格局更是處處都顯露出“以小見大”的士人寫作傳統,因此在文風血脈上,汪老的文章可謂與晚明的張岱、近世的周作人等一脈相承,是為真正的“文人文章”。再加上老師沈從文的影響,汪老的散文中可謂同時繼承了明清小品和五四散文這古今兩大傳統。正是這兩大傳統,造就了汪老文字間具有一種散淡閑適的風格,然而這種散淡閑適卻又不同于魏晉和晚明的“與世無爭”,卻是另具一種空靈的美感。于是,讀汪老筆下的美食,盡管大多為一些尋常食物,讀來卻是別有一番風味。
汪老雖在飲食哲學上崇尚“雜博”,卻并不表示他就贊成“食無禁忌”。在汪老的筆下,也是有“不吃為宜”的,“炒肉芽”即為其一。前幾年非典盛行,據傳就是國人“亂吃”造成的惡果,盡管這種說法的真實性值得質疑,但飲食上的“百無禁忌”卻的確值得反思。寬容如汪老者,早就注意到了這一點。可見,任何閑適和散淡也都是有“邊界”的吧。
最后想說一說的是,讀著汪老寫的那些美食,總覺著很像是現代人寫的微博,只要是特色鮮明、令人印象深刻的美食,大多都逃不出汪老的那支筆。所以,無論是在寫五湖四海的風土人情,還是回憶少時鄉間的傳奇,兜兜轉轉,總會跳出一兩種令人難忘的吃食呈現在讀者面前,這種記錄“強迫癥”可不是正如現代人刷微博。經不住的是,汪老的那支妙筆會“生花”,再怎么平常的民間小吃或家常小菜,經過汪老的描寫,就都是一盤活色生香的點心或菜肴,直叫人垂涎欲滴。汪老這種“功夫”寫就的文字,比起那些“深夜慎入”的美食圖片來,“殺傷力”可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
毛不吃抹布,腿不吃板凳,蕎麥不吃死人,小蕎麥不吃蒼蠅。
——王曾祺談吃
汪曾祺“食材”的培育
在汪曾祺的眾多隨筆中,有關飲食文化的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們熟悉“端午節鴨蛋”、“蠶豆”、“豆腐”、“茶館”……關于汪曾祺的美食文章的書籍越來越多。從書名中,我們可以一眼看出,如《五味》、《趣》、《四方菜》、《家鄉菜》、《汪曾祺談菜》等。如果說汪曾祺是“吃”的“典范”,那么至少應該有三個標準:會吃、會做、會吃。
會吃
汪曾祺的生活軌跡使他對家鄉昆明、張家口和北京的飲食十分熟悉。他經常談論如何吃某種食物,并能舉出不同地方不同的飲食習慣。不僅如此,他還可以說最吸引人的時間和最適合烹飪食物的方法。虎頭鯊、蒼壽魚、硯螯合劑、蝸牛、蛤蜊、野鴨、鵪鶉、斑鳩、十二指腸;)龍蒿、枸杞、馬齒莧、馬齒莧等。不僅吃各種各樣的食物,吃的范圍也很廣,然后用閑散隨意的詞語來形容給我們聽,傳達的信息并不是“纏綿的牙齒”所能覆蓋的無限魅力。在《willeat》這一點上,一直出乎意料。
他也很好吃。從他說的許多關于吃的事情來看,他只是一個吃得很方的人。從家鄉高郵的鴨蛋到北京的豆汁,再到湖南的咸肉,包括腌菜、腌菜和野菜,他都要去調查和思考。我總是想表達我毫不掩飾的欽佩之情:我從來沒有吃過像昆明這么好的牛肉。(王曾祺老人)
除了生吃,洋花蘿卜也可以和蘿卜絲混合食用。蘿卜斜切成片,然后切成細絲,加入醬油、醋、麻油拌勻,撒上少許蒜,十分開胃。童謠:人生之初,流鼻涕。油和胡蘿卜炒飯。在農村,蔥炒飯是一種美味佳肴,所以蘿卜絲吃起來很美味。蘿卜絲和切得很細的海蜇皮在我的家鄉是一頓大餐。它也是一道涼菜,配以干薺菜、咸蝦和松子。北京人把蘿卜切成片加水,然后煮羊肉湯。它嘗起來又輕又好吃。(蘿卜)
“吃遍天下”可以說是對汪曾祺“飲食能力”最恰當的評價,而他文章中所表現的不同地域和地區的飲食風格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一個廣泛而深刻的方面。
可以做
食物是庇護所的基礎。每件事都不應該一絲不茍,尤其是飲食。在中國,許多菜肴都是用不起眼的食材制作而成,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精致”食物,它們已經成為世界上最美味的菜肴。那么,汪曾祺自己的“苛求”水平是什么呢
如果我們從專業廚師的角度來看待汪曾祺的烹飪,肯定是不夠的。汪曾祺在文章中坦承,他只會做家常菜。“我不會做大菜。”當我去海南島的時候,主人送給我很多魚翅和燕窩。我沒有搬到那里,因為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汪曾祺很擅長做家常菜。汪曾祺的烹飪技藝在當時文壇上享有盛譽。因此,每當港臺作家或外國汪曾祺研究員來北京采訪汪曾祺時,中華全國總工會并不安排客人在酒店用餐,而是直接讓客人在汪曾祺家中用餐。有一次,一位法國客人來采訪汪曾祺,汪曾祺為他做了一種鹽水煮豆。法國人第一次吃了用鹽水煮熟的黃豆,甚至還吃了黃豆的殼。
一位臺灣女作家來到北京,請我為她做一頓飯。我給她做了幾道菜,其中一道菜是燒蘿卜。她贊不絕口。當然,這并不壞:這兩天是吃蘿卜的最佳時間,蘿卜都很大,但仍然很嫩,不是麩皮;它們和干貝一起煮。她說臺灣沒有這種蘿卜。美籍華裔女作家聶華玲和她的丈夫安琪兒來到北京,要在我家吃飯,我親自下廚。我給她上了幾道菜。我忘了幾道菜。我只記得一大碗干絲。華玲把它吃得精光,最后拿起碗,把剩下的湯喝了。華玲來自湖北省。當他年輕的時候,他煮過干絲綢。但是在美國吃東西并不容易。
光會吃,會做吃的還不能算上是個行家,還要窺得“吃”中的門道,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這對于一個人的文化底蘊要求較高,而這也是汪曾祺的散文具有“文化”特點的原因。汪曾祺在散文中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和融入,詩經、古人筆記乃至于中國地域的地方風俗,使得文字總是給人親切感和共鳴感。
汪曾祺小時候讀漢樂府《十五從軍征》,很為詩中的“真情”而感動,但他始終沒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現在各地植物稱作“葵”,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這些植物葉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來讀到清朝吳其睿的《植物名實圖考》,才知道吳氏把“葵”列為蔬類的第一品。吳氏經過考證,激動地說“葵”便是南方幾省還有種植的“冬莧菜”。“采葵持作羹”說白了,就是冬莧菜稀飯……
由此可見可見“葵”到清朝已經淪為無人知曉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詩經》就有記載,后魏《齊民要術》,元代王禎的《農書》都把它列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測可能是后來全國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見,“蔬菜的命運,也和世間一切事物一樣,有其興盛和衰微,提起來也可叫人生一點感慨。
從平常的“吃食”中寄寓著人事的興衰慨嘆,這的確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獨特表現方式和精深之處。汪曾祺說:“草木蟲魚,多是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對于草木蟲魚有興趣,說明對人也有廣泛的興趣。”(注:汪曾祺:《隨筆兩篇〈葵·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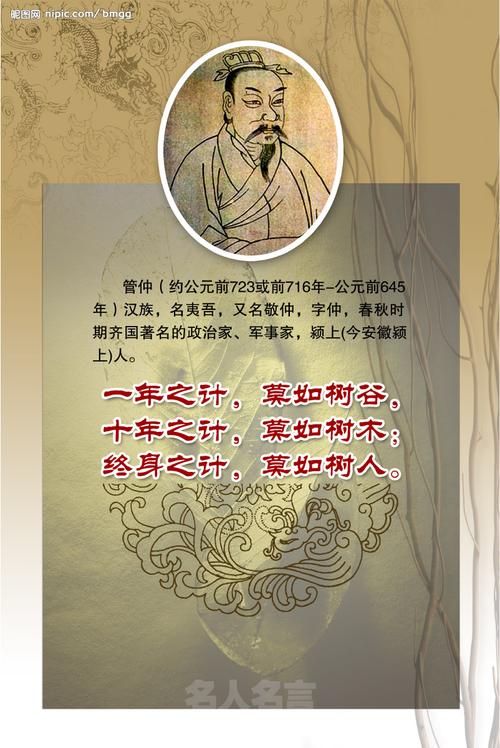
本文發布于:2023-12-18 14:59:13,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本文鏈接:http://www.newhan.cn/zhishi/a/1702882753247269.html
版權聲明:本站內容均來自互聯網,僅供演示用,請勿用于商業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在24小時內刪除。
本文word下載地址:2022關于汪曾祺談吃的散文.doc
本文 PDF 下載地址:2022關于汪曾祺談吃的散文.pdf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