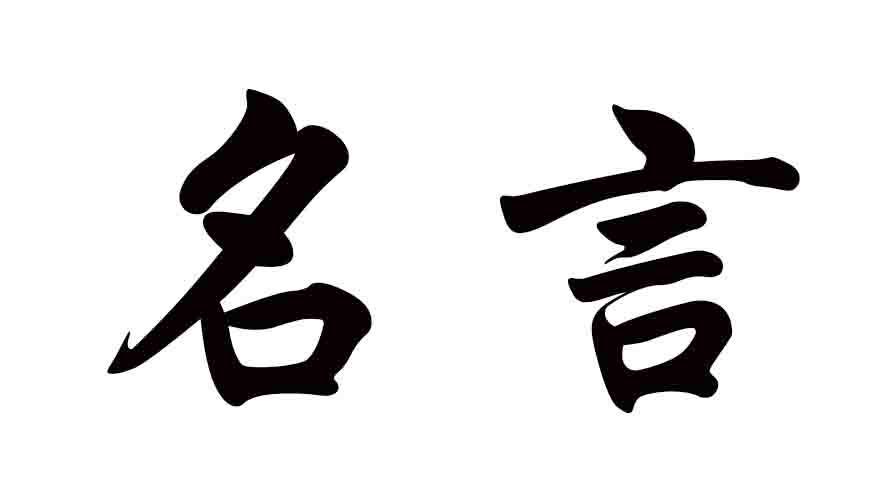
想象鄉土的方式
作者:傅華 董愛宇
來源:《藝術廣角》2022年第01期
20世紀90年代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隨著現代化與城鎮化的推進,中國鄉村進入劇烈的轉
型期,鄉土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面臨沖擊。一些表現新世紀農村的作品應運而生,新
鄉土書寫暗潮涌動。2005年6月,《佛山文藝》聯合《山花》舉辦“黔東南筆會”,討論“和諧
社會與文學承擔”的話題,一系列關于“新鄉土”如何契合和諧社會發展的討論由此展開。翌年
六月,由《佛山文藝》發起,《人民文學》《小說選刊》《莽原》及新浪網共同舉辦“新鄉土
文學征文大賽”,眾多鄉土作家參與其中,文能、王山對“新鄉土文學”有所界定。[1]2007年3
月,《佛山文藝》召開“新鄉土文學”研討會。關于“新鄉土文學”的探討在持續發酵。2015年,
《雨花》提出“新鄉土寫作”概念,面向全國征集“新鄉土寫作”長篇小說,并在《雨花·中國作家
研究》上以“長篇小說大展”的方式連續六期刊發,引起了廣泛關注。[2]隨后,第二屆中國長篇
小說高峰論壇在江蘇師范大學召開,“新鄉土寫作”是此次會議的熱門話題,與會專家一致肯定
“新鄉土寫作”的價值,“新鄉土寫作”成為當下學界關注的熱點之一。
綜合學界的探討,“新鄉土寫作”大致呈現出如下特征。從寫作時間上看,“新鄉土寫作”是
指新世紀以來的中國鄉土文學創作。從寫作主體上看,主要是指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及70
年代后期的青年作家,他們大多有短暫的農村生活經歷。從寫作內容與對象來看,書寫的是轉
型與裂變中的新世紀農村社會。這里不僅體現了農村范圍的擴大:從原鄉到城鄉接合部再到城
中村,而且也體現了農民身份的變化:從地道的農民到流動在城鄉間的打工人再到定居城市的
進城務工者。同時,農村人際關系的變更、人與土地關系的變化等,都是“新鄉土寫作”關注的
焦點。從寫作視角來看,“新鄉土寫作”要求作家轉換“回看”下的“俯視”姿態,代以平等地、歷
史地、整體地展示新鄉土經驗的寫作視角;避免簡單情感判斷下的一元價值取向,代之對農村
社會現實的智性反思與多維審視。新變的鄉土與人心、爭鳴的寫作與批評,使得正處于進行狀
態的“新鄉土寫作”呈現出多元興盛的面貌,成為新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學界對這股
蔚為壯觀的“新”創作潮流也展開了廣泛的探討與研究,以期激活傳統“鄉土文學”的“現代性”。
一、“離土”或“在土”的鄉土想象
“鄉土文學”作為一個世界性的文化母題,在不同國別、不同時代有著不一樣的書寫,縱然
變化多端但其創作之根都植于土地。不管是美國南北戰爭時期費尼莫·庫珀的“邊疆小說”、布
雷特·哈特代表的西部文學,19世紀70年代意大利興起的“真實主義”的“鄉土小說”文學流派,
[3]還是中國鄉土文脈中以魯迅為代表的批判型鄉土文學、沈從文等代表的抒情型鄉土文學,
抑或是柳青等代表的革命型鄉土文學和韓少功等代表的尋根型鄉土文學,[4]“土地”始終是其敘
事的內核。正如李敬澤所言:“現代文學以來,土地在不同時期的鄉土寫作中都是一個意義中
心,它是歷史的焦點,也是農民可以安身立命的終極價值。”[5]
中國作為農業大國,土地是農民生活最基本的保障。農民對土地的依賴與感情,在千百年
集體無意識的積淀下形成了對土地近乎神圣的崇拜。傳統鄉土作家大多書寫了自己與土地的深
厚情感。從小與土地的深刻聯結,使他們的“根”深扎于土,厚重的鄉土記憶和熟悉的鄉土經驗
讓他們的鄉土想象都有根基,鄉土寫作呈現出一種“系于土”的生命形態。
反觀“新鄉土”寫作者,他們雖生于鄉村,但鄉土經驗相對短暫且有限。時間與空間距離的
間隔使鄉土記憶與感情淡化,原本就浮在表層的鄉土之根漸次松動,作家與鄉土逐漸陌生,以
致于產生了隔膜。徐則臣就坦然說出自己的隔膜:“我對當下的鄉村越來越陌生,我覺得沒有
足夠的能力把握好鄉村。”[6]這不僅是徐則臣的問題,更是新鄉土作家的共同難題。他們未曾
親歷鄉土的種種變化,難以感知當下城鄉之間的復雜關系。“新鄉土寫作”一旦失去了具體新鮮
的“在土”體驗,就易流于認知的表象,從而在內容、情感的表達上出現隔膜,乃至失真,甚至
走向個人意識與現實鄉土的錯位。
不可否認,“新鄉土寫作”中也有不少親于土、系于土的佳作。葉煒在談及其“鄉土中國三
部曲”的寫作時,直言:“我從未離開過那片土地”“為了寫作《富礦》,我先后多次返鄉,深入
煤礦考察;為了寫作《后土》,我對老家的鄉村干部進行采訪,積累了厚厚的一摞資料;為了寫
作《福地》,我廣泛搜集資料,調動自己的全部鄉村生活經驗。”[7]實地調查采訪、收集資
料,躬身拾掇新的鄉土經驗,正是葉煒能夠寫出麻莊這個復雜且真實的典型中國農村的原因。
與鄉土存在隔膜是不少新鄉土作家真實的寫作境遇,付秀瑩也感嘆過:“這么多年了,我寫下
的,大約不過是記憶中的鄉土。在那些小說里,更多的是追憶。”[8]童年記憶中的鄉土與現今
的鄉土無疑千差萬別,付秀瑩清醒地知道自己與鄉土的“隔”,也在努力地修復和逾越這道
“隔”。她每天都與父親打電話,了解父親的一日三餐,了解“芳村的每一戶人家,婚喪嫁娶,
愛恨冤仇,鄉村內部的肌理和褶皺”和“鄉村人情世故的每一個拐彎抹角處”。[9]一通通的電
話、一次次的往返,付秀瑩直面實在的鄉村經驗,寫出了當下鄉村的生活與情感狀態。像付秀
瑩這樣深度地進入鄉土的作家才能寫出真實的、鮮活的鄉土世界。
既是參與者又是敘述者的李娟,正是得益于對牧民生活的完全融入,才能在《冬牧場》中
翔實地展示哈薩克牧民們不斷“轉場”、一直“在路上”的艱苦生活。為了對當下農村情況進行有
效考察與反映,2008到2009年間,梁鴻回到家鄉梁莊,以“非虛構寫作”的紀實方式展示新鄉
土的變遷。五個多月的時間里,梁鴻以平等的姿態同老家農民展開了深入的對話與交流,最后
將所有內容集結成《中國在梁莊》。2011年,為完成《出梁莊記》,梁鴻花費了兩年時間,
奔赴全國各地探訪“出走”梁莊的農民,與之同吃同住,真切體會他們的艱辛。在與土地和農民
近距離的接觸中,梁鴻與梁莊建立了深刻的情感與精神聯結,這使得梁鴻能夠對在現代化沖擊
下梁莊的“常”與“變”進行具象的呈示。梁鴻對變遷中梁莊人真實的生存狀態予以了相對客觀的
再現,同時也寄托了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對當下鄉土與農民未來命運的關注和思考。
二、“審丑”或理想化的鄉土想象
有些作家在談論鄉土時總會下意識地與落后、貧窮、閉塞等相聯系,并通過對它們的批判
來呼喚“美”的所在,或者簡單地設想鄉土未來的光明前景,打造虛浮的鄉土“烏托邦”。“審丑”
意識與理想化的期許一直潛藏于鄉土文學的創作中。
新世紀以來,鄉土在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中不斷遭受沖擊和洗禮。在現代文明的映照下,貧
困的鄉土裸露出人性的黑暗和丑惡。如果說閻連科的系列傳統鄉土作品聚焦“耙耬山脈”大量書
寫苦難,以“審丑”或苦難意識揭示鄉土的落后、愚昧甚至黑暗,那么魯敏等“70后”新鄉土作家
也在“審丑”中追問鄉土的罪與惡。“暗疾”是魯敏一部小說的名字,也是其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
主題。在小說《暗疾》中,魯敏夸張化地為每個人都設置了“暗疾”:父親的“神經性嘔吐”、母
親對記賬的病態癡迷、姨婆對“大便”的變態關注。還有《取景器》中,女攝影師對破敗丑相近
于變態的癡迷。魯敏如考究者一般,拿著放大鏡仔細觀摩眾生身心的隱疾,并展示給讀者一同
觀看。但魯敏與一些作家僅描繪生理層面的痛苦體驗與表象的丑陋不同,她沒有一味沉溺于
“丑”的展覽,而是試圖對其精神動因展開深層的剖析,努力揭示精神“暗疾”。畢竟“丑”的展示
終究不是目的,在人的掙扎與自我拯救中散發出人性的光輝,才是“審丑”的精神訴求與終極意
義。《后土》《中國在梁莊》與《陌上》等作品沒有故作姿態地渲染鄉土的“丑”,他們更關心
的是鄉村在艱難轉型中的精神裂變,同樣是對鄉土“丑”的敘述,但做到了對簡單展覽式“審丑”
的超越。
新鄉土文學的“審丑”還集中出現在對權力、暴力與性的揭露上。《陌上》中芳村首富大全
為一己私利操縱選舉,讓建信當上村支書;擴軍在村委會小白樓前大張旗鼓地分發電飯鍋、豆
漿機公然賄選。《陌上》對資本和政治合謀的揭示,呈現了鄉村政權中的陰暗面。暴力與性的
符碼也大量充斥在新鄉土作品中。苦難、暴力與性確是鄉土真實面貌的一部分,出現在鄉土文
學敘述中本無可厚非,但一味沉淪于“審丑”之中甚至流于單純的感官刺激則需警惕。他們對鄉
土丑態的過分渲染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文本的多元意義,丟掉了鄉土寫作的初衷。旁觀的姿
態、對信息的多次加工等,都易使作家不自覺地將鄉土的丑惡夸張化甚至妖魔化。這樣的創作
顯然無法觸摸到滋生苦難、強權等“丑行”的鄉土大地的復雜肌理,也不能深刻洞察產生這類丑
行的內在動因。
與“審丑”相對的另一寫作傾向,是對鄉土未來命運的一廂情愿式的美好想象。一些作家看
到了新鄉土發展中的諸多問題,但囿于他們的“土性”不足,對鄉土問題認識表面化,文本呈現
的解決方案相應流于簡單化與理想化。葉煒的《后土》也有此嫌疑。他展示了都市文明沖擊下
麻莊不斷變化的面貌,盡管鄉土變遷、人心變化,麻莊的村民仍有自己的夢想。他們夢想在家
門口就能工作,夢想住上漂亮寬敞的小康樓,夢想搭上致富的列車……如何幫助麻莊村民實現
夢想,葉煒給出了自己的方案。用劉非平的話說,就是:“建設小龍河觀光帶、葦塘觀鳥園、
果園采摘園、馬鞍山野味館、麻莊魚塘垂釣中心等,以觀光旅游帶動麻莊的經濟發展,帶動麻
莊鄉親共同致富。”[10]雖然在小說結尾,這幅美好的“鄉村藍圖”確實實現了,小康樓建成、景
觀帶竣工、旅游公司成立、超級大農場也在籌備中,整個村莊的未來光明無限,這無疑折射出
當今脫貧攻堅后的鄉村振興圖景,但又不免有過于理想化之嫌。
憑借鄉土資源來發展旅游業、經營生態經濟,這種發展模式還散見于眾多作家作品之中,
包括一些浸淫鄉土寫作已久的作家。周大新《湖光山色》中,楚暖暖依靠楚長城和丹江湖建起
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帶領楚王莊共同富裕。關仁山《金谷銀山》里,范少山憑借傳奇的金谷
種,帶領大家建設金谷子種植基地,又開山修路、利用天然溶洞發展旅游業。這些作品都暢想
了新農村美好的前景,但其成功致富的過程充滿了偶然性與傳奇性,畢竟并非每個農村都能坐
擁綠水青山、文化遺址或是“金種子金蘋果”。且就鄉土旅游業而言,其巨大的資金投入、較長
的建設周期、復雜的管理運營等都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因此綠色生態農業、鄉土旅游經濟毋庸
置疑是新世紀鄉村發展的可行思路,但其普適性不高。由此可見,葉煒等對鄉土問題的簡單化
處理,有捉襟見肘之處,他們筆下的“烏托邦”式的鄉土美好理想終究難以應對新鄉土現實的復
雜性。但其間呈現出的這群知識分子對新鄉土未來出路的關注與思考、責任與擔當也不能簡單
否定。
相比較走綠色發展道路,開礦挖煤、開山取石、攔河取沙、棄耕辦廠這些成本低、見效快
的致富方式明顯更容易被農民接納。但這種破壞式發展帶來的污染等生態問題令人堪憂,經濟
體制變化和人心浮動帶來的不確定性也暗藏隱患,《陌上》就真實地書寫了上述隱憂。在皮革
行業的暴利誘惑下,村北的莊稼地變成了大片的廠房。不少人憑借皮革生意致富,但隨之而來
的是無人敢喝地下水、空氣又酸又臭、怪病越來越多。芳村的發展困境也是中國大多數鄉村面
臨的共同難題。對于現實發展的難以把控,付秀瑩深感無奈。既然變化無常,付秀瑩便以“不
變”應“萬變”,以細碎的、片段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即“一種結構的未完成狀態”來“遙遙呼應著
這個世界多變現實所蘊含的無限未知”。[11]
在復雜多元的時代背景下,新鄉土作家對于鄉土的想象繁雜不一。在未完成狀態書寫中呈
現新鄉土中異質、陌生、未知的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這對“新鄉土寫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若只停留于對新世紀鄉土問題的簡單認識與判斷,僅僅是展覽式的“審丑”或理想化的處理,
“新鄉土寫作”將陷入更深的困境。
三、鄉土想象的困境
面對只沉迷于過往經驗或單純地想象鄉土、只浮于表面而蒼白無效的某些鄉土寫作,一些
學者發出“新鄉土文學距離鄉村有多遠”[12]的質疑。因為作家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融入鄉土
大地,才能契合新世紀鄉土變幻的步伐,才能準確揭示鄉土變化的新質。“在土”體悟的缺失不
僅會使情感失真,也易導致判斷失效。是懷念傳統鄉土而抗拒甚至恐懼城市的侵襲?還是融入
城市進入城鄉一體后的新生?鄉土現實的變遷加劇了作家價值取向的裂變與分化,鄉土中命運
與情感的困厄困惑也導致了他們價值立場的曖昧與猶疑。于是,在與土地和農民的若即若離
中,在自我身份認同與價值認同的諸多困惑中,部分新鄉土作家的創作表現出現代主體的迷
茫。這迷茫不局限于其個人,更是“新鄉土寫作”難以規避的現實境遇與精神難題。
二、“審丑”或理想化的鄉土想象
有些作家在談論鄉土時總會下意識地與落后、貧窮、閉塞等相聯系,并通過對它們的批判
來呼喚“美”的所在,或者簡單地設想鄉土未來的光明前景,打造虛浮的鄉土“烏托邦”。“審丑”
意識與理想化的期許一直潛藏于鄉土文學的創作中。
新世紀以來,鄉土在傳統與現代的沖突中不斷遭受沖擊和洗禮。在現代文明的映照下,貧
困的鄉土裸露出人性的黑暗和丑惡。如果說閻連科的系列傳統鄉土作品聚焦“耙耬山脈”大量書
寫苦難,以“審丑”或苦難意識揭示鄉土的落后、愚昧甚至黑暗,那么魯敏等“70后”新鄉土作家
也在“審丑”中追問鄉土的罪與惡。“暗疾”是魯敏一部小說的名字,也是其小說創作的一個重要
主題。在小說《暗疾》中,魯敏夸張化地為每個人都設置了“暗疾”:父親的“神經性嘔吐”、母
親對記賬的病態癡迷、姨婆對“大便”的變態關注。還有《取景器》中,女攝影師對破敗丑相近
于變態的癡迷。魯敏如考究者一般,拿著放大鏡仔細觀摩眾生身心的隱疾,并展示給讀者一同
觀看。但魯敏與一些作家僅描繪生理層面的痛苦體驗與表象的丑陋不同,她沒有一味沉溺于
“丑”的展覽,而是試圖對其精神動因展開深層的剖析,努力揭示精神“暗疾”。畢竟“丑”的展示
終究不是目的,在人的掙扎與自我拯救中散發出人性的光輝,才是“審丑”的精神訴求與終極意
義。《后土》《中國在梁莊》與《陌上》等作品沒有故作姿態地渲染鄉土的“丑”,他們更關心
的是鄉村在艱難轉型中的精神裂變,同樣是對鄉土“丑”的敘述,但做到了對簡單展覽式“審丑”
的超越。
新鄉土文學的“審丑”還集中出現在對權力、暴力與性的揭露上。《陌上》中芳村首富大全
為一己私利操縱選舉,讓建信當上村支書;擴軍在村委會小白樓前大張旗鼓地分發電飯鍋、豆
漿機公然賄選。《陌上》對資本和政治合謀的揭示,呈現了鄉村政權中的陰暗面。暴力與性的
符碼也大量充斥在新鄉土作品中。苦難、暴力與性確是鄉土真實面貌的一部分,出現在鄉土文
學敘述中本無可厚非,但一味沉淪于“審丑”之中甚至流于單純的感官刺激則需警惕。他們對鄉
土丑態的過分渲染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文本的多元意義,丟掉了鄉土寫作的初衷。旁觀的姿
態、對信息的多次加工等,都易使作家不自覺地將鄉土的丑惡夸張化甚至妖魔化。這樣的創作
顯然無法觸摸到滋生苦難、強權等“丑行”的鄉土大地的復雜肌理,也不能深刻洞察產生這類丑
行的內在動因。
與“審丑”相對的另一寫作傾向,是對鄉土未來命運的一廂情愿式的美好想象。一些作家看
到了新鄉土發展中的諸多問題,但囿于他們的“土性”不足,對鄉土問題認識表面化,文本呈現
的解決方案相應流于簡單化與理想化。葉煒的《后土》也有此嫌疑。他展示了都市文明沖擊下
麻莊不斷變化的面貌,盡管鄉土變遷、人心變化,麻莊的村民仍有自己的夢想。他們夢想在家
門口就能工作,夢想住上漂亮寬敞的小康樓,夢想搭上致富的列車……如何幫助麻莊村民實現
夢想,葉煒給出了自己的方案。用劉非平的話說,就是:“建設小龍河觀光帶、葦塘觀鳥園、
果園采摘園、馬鞍山野味館、麻莊魚塘垂釣中心等,以觀光旅游帶動麻莊的經濟發展,帶動麻
莊鄉親共同致富。”[10]雖然在小說結尾,這幅美好的“鄉村藍圖”確實實現了,小康樓建成、景
觀帶竣工、旅游公司成立、超級大農場也在籌備中,整個村莊的未來光明無限,這無疑折射出
當今脫貧攻堅后的鄉村振興圖景,但又不免有過于理想化之嫌。
憑借鄉土資源來發展旅游業、經營生態經濟,這種發展模式還散見于眾多作家作品之中,
包括一些浸淫鄉土寫作已久的作家。周大新《湖光山色》中,楚暖暖依靠楚長城和丹江湖建起
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帶領楚王莊共同富裕。關仁山《金谷銀山》里,范少山憑借傳奇的金谷
種,帶領大家建設金谷子種植基地,又開山修路、利用天然溶洞發展旅游業。這些作品都暢想
了新農村美好的前景,但其成功致富的過程充滿了偶然性與傳奇性,畢竟并非每個農村都能坐
擁綠水青山、文化遺址或是“金種子金蘋果”。且就鄉土旅游業而言,其巨大的資金投入、較長
的建設周期、復雜的管理運營等都是不容忽視的因素。因此綠色生態農業、鄉土旅游經濟毋庸
置疑是新世紀鄉村發展的可行思路,但其普適性不高。由此可見,葉煒等對鄉土問題的簡單化
處理,有捉襟見肘之處,他們筆下的“烏托邦”式的鄉土美好理想終究難以應對新鄉土現實的復
雜性。但其間呈現出的這群知識分子對新鄉土未來出路的關注與思考、責任與擔當也不能簡單
否定。
相比較走綠色發展道路,開礦挖煤、開山取石、攔河取沙、棄耕辦廠這些成本低、見效快
的致富方式明顯更容易被農民接納。但這種破壞式發展帶來的污染等生態問題令人堪憂,經濟
體制變化和人心浮動帶來的不確定性也暗藏隱患,《陌上》就真實地書寫了上述隱憂。在皮革
行業的暴利誘惑下,村北的莊稼地變成了大片的廠房。不少人憑借皮革生意致富,但隨之而來
的是無人敢喝地下水、空氣又酸又臭、怪病越來越多。芳村的發展困境也是中國大多數鄉村面
臨的共同難題。對于現實發展的難以把控,付秀瑩深感無奈。既然變化無常,付秀瑩便以“不
變”應“萬變”,以細碎的、片段的想象世界的方式,即“一種結構的未完成狀態”來“遙遙呼應著
這個世界多變現實所蘊含的無限未知”。[11]
在復雜多元的時代背景下,新鄉土作家對于鄉土的想象繁雜不一。在未完成狀態書寫中呈
現新鄉土中異質、陌生、未知的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這對“新鄉土寫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若只停留于對新世紀鄉土問題的簡單認識與判斷,僅僅是展覽式的“審丑”或理想化的處理,
“新鄉土寫作”將陷入更深的困境。
三、鄉土想象的困境
面對只沉迷于過往經驗或單純地想象鄉土、只浮于表面而蒼白無效的某些鄉土寫作,一些
學者發出“新鄉土文學距離鄉村有多遠”[12]的質疑。因為作家只有真正沉下去,才能融入鄉土
大地,才能契合新世紀鄉土變幻的步伐,才能準確揭示鄉土變化的新質。“在土”體悟的缺失不
僅會使情感失真,也易導致判斷失效。是懷念傳統鄉土而抗拒甚至恐懼城市的侵襲?還是融入
城市進入城鄉一體后的新生?鄉土現實的變遷加劇了作家價值取向的裂變與分化,鄉土中命運
與情感的困厄困惑也導致了他們價值立場的曖昧與猶疑。于是,在與土地和農民的若即若離
中,在自我身份認同與價值認同的諸多困惑中,部分新鄉土作家的創作表現出現代主體的迷
茫。這迷茫不局限于其個人,更是“新鄉土寫作”難以規避的現實境遇與精神難題。

本文發布于:2023-11-12 08:02:24,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本文鏈接:http://www.newhan.cn/zhishi/a/1699747344213339.html
版權聲明:本站內容均來自互聯網,僅供演示用,請勿用于商業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在24小時內刪除。
本文word下載地址:想象鄉土的方式.doc
本文 PDF 下載地址:想象鄉土的方式.pdf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