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乙訪談:好作家的爛作品給我信心
文 | 阿乙 胡少卿 受訪人:阿乙,作家采訪人:胡少
卿記錄人:余欣采訪手記:余欣采訪時間: 2013年5月7
日下午14:00-15:30采訪地點(diǎn):北京某咖啡館本采訪稿內(nèi)容已
經(jīng)受訪人授權(quán) 胡少卿:在你列出的影響你的作家名單中,
有兩個不太常見的名字:皮蘭德婁和阿利桑德羅·巴里科。
先談?wù)勀銓@兩個作家的感受。阿乙:皮蘭德婁和巴里科的
書在中國不是特別流行。皮蘭德婁,上次有個意大利學(xué)漢學(xué)
的,他問我,你喜歡哪個意大利作家,我就讀過這么一兩個。
像卡爾維諾,幾次都讀不下去,主要是讀了《寒冬夜行人》
開頭,那個廢話,從第一行可以刪到第二十行。我看了這個
就一直沒讀下去,然后可能就錯過這個作家了。皮蘭德婁在
中國沒有幾本書,我只買到一本,譯者叫“廈大六同人”。
翻譯質(zhì)量是這樣:可能有一兩篇翻得還挺好,剩下的就翻得
不行。不過,皮蘭德婁的每個故事都好,經(jīng)得起翻譯的糟蹋。
我覺得皮蘭德婁是一個精品作家,他在很深的程度上,關(guān)心
人本身。王安憶在“短經(jīng)典”總序里,轉(zhuǎn)述了一個他的故事:
一個有家族遺傳病的人,他用各種方式,鍛煉、節(jié)欲、飲食
調(diào)理等等,最后突破了那個生命規(guī)律,也就是說,可能他的
祖父、父母只能活到多少歲,但他突破了這個歲數(shù)。然后他
自殺了。這就是皮蘭德婁的故事。我還記得他另一篇寫自殺
的。一個人打定主意去自殺,心意特別堅決,但是在路上,
被一個熟人拉去類似卡拉OK、大排檔的地方轉(zhuǎn)了大半夜。
這就很荒謬。一個人要去自殺,路上被一個朋友給帶走了。
朋友問他,你有什么事嗎?他不能說“我去自殺”,所以跟
著朋友大半夜。最后他只好返回家里,快要到家的時候,在
車上吧,很倉促地把毒藥吃了。你就感覺很悲涼:人連自己
的死亡都決定不了。就好比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兩個人喜
歡了很久,就要搞起來的時候、很神圣的時候,突然被什么
事延誤了。我早期寫的《自殺之旅》就是模仿皮蘭德婁這篇。
皮蘭德婁可以很多年后重讀,而巴里科是你讀第一遍挺喜
歡,讀第二遍的時候就挺厭惡。巴里科可以定位為小資作家。
他就那么幾招,其中一招是:先把東西弄得特別好,女人就
很美,男人就特別有才,像那個海上鋼琴師,然后把他們又
弄得特別孤獨(dú),最后讓他們無可挽回地碎掉,毀滅掉,然后
讓你心里有個巨大的落差,你讀著讀著感動得就哭了。這個
模式基本上就是小資作品的全部秘密。村上春樹也逃不開這
個。這樣的小說是可以批量生產(chǎn)的,跟人的痛苦沒關(guān)系,是
人的一杯咖啡。胡少卿:以前的訪談中你提到最喜歡三本書:
《局外人》,《慢》,《茶花女》。這個名單現(xiàn)在有變化嗎?阿
乙:現(xiàn)在可以擴(kuò)充一下,《罪與罰》。還有福克納的什么我都
喜歡:《八月之光》,《押沙龍,押沙龍!》,《喧嘩與騷動》。
福克納的每一部都經(jīng)得起推敲。胡少卿:你的《下面,我該
干些什么》里的那種緊張感有點(diǎn)像《罪與罰》。阿乙:最開
始是想模仿《罪與罰》,后來發(fā)現(xiàn)能力不夠,推倒重來又按
《局外人》的路子去寫。胡少卿:現(xiàn)在看來,這部小說有點(diǎn)
像《罪與罰》與《局外人》的混合體。結(jié)尾那個“我”的振
振有詞有點(diǎn)不符合他的學(xué)生身份了。阿乙:有道理。可能90%
寫作的人都會犯的一個毛病是,寫小說的時候,結(jié)尾都是最
先浮現(xiàn)在心里的。那個謎底早就在心里了。等你耗盡半年時
光,終于寫到結(jié)尾的時候,你就失態(tài)了。胡少卿:迫不及待
要把這個結(jié)尾安上去?阿乙:不是安上去,是你一開始寫的
時候,這個結(jié)尾就存在。如果它是在戲劇里面,就很好。放
在小說里有點(diǎn)突兀,因為前面我太服從小說的規(guī)律了。前面
筆法壓得挺好,一路在壓,壓抑自己,讓自己不展示什么,
里:為什么他要這么撞一下?他可以不撞,不撞的話他就成
球王了。當(dāng)然,這也可能是為了給自己偷懶編的理由。我改
東西已經(jīng)改得太苦了。胡少卿:看得出來你的文字是很講究
的,是嘔心瀝血出來的。和早期余華很像。你的許多語調(diào)、
語句都非常之余華。阿乙:早期特別是這樣。2004年《新京
報》同事蕭三郎約我寫一篇余華的書評。我想,我要進(jìn)軍書
評行業(yè)了。因為是第一次寫書評,很隆重,把上海文藝出的
那套余華都買齊了,集中讀了十天還是九天。突然讀到中文
有這么好的作家,中他的毒就很深,那個時候我剛剛要開始
寫作。胡少卿:28歲才開始讀余華……余華對你來說,有點(diǎn)
不用再期待了。胡少卿:《兄弟》是2005年出版的,余華沉
默了又將近十年了。阿乙:是噢,真快。人生有幾個十年。
胡少卿:你的小說里我印象尤其深的是兩個短篇:《小人》
和《楊村的一則咒語》。《小人》的技巧很完善。小說里那個
中學(xué)老師叫陳明義,你把“義”字寫成了繁體,是不是有你
的講究?阿乙:用繁體字說明他的那種自我期許,他有追求,
他是一個讀書人,他對《孝經(jīng)》有了解。胡少卿:繁體的“義”
字,上面是個“羊”,底下是個“我”。我讀時產(chǎn)生了“我是
羔羊”這么一種聯(lián)想——他是無辜的。阿乙:這個解釋挺好
的,我還沒想到呢,第一次聽人這么說。胡少卿:這個小說
的包袱藏得特別深,許多搞評論的都沒看出來。鑰匙就在小
說最后一句:“李喜蘭便哭,便喊便叫,你這個騙子,你騙
了陳明義又來騙我,你這個騙子。”阿乙:小說設(shè)計的時候
很危險,各種走鋼絲。最后一句話要把前面搭起來的堅固的
大廈抽走一根線,整個的塌掉,然后就看到另外一棟建筑物
在里頭。胡少卿:看到最后一句的時候脊背發(fā)冷,想這個人
怎么這么陰險。實(shí)際上兇手還是那個看似被冤枉的馮伯韜。
阿乙:我當(dāng)時寫的時候蠻興奮的,前后寫了一個月,各種謀
算,實(shí)際上是想講一個完美的故事。玩故事是我的一個追求。
我一生想玩這么三四篇故事。不過《小人》里有一個漏洞,
就是這個人為了下棋輸了去把另一個人殺掉,合法性不夠。
胡少卿:另一篇,《楊村的一則咒語》獲得過蒲松齡短篇小
說獎。故事是你從楊繼斌那里聽來的。小說和他講的故事之
間有多大的距離呢?阿乙:殼子等于說是他講的。這個事發(fā)
生在他的村莊,所以叫楊村。有兩個人因為一只雞賭咒,就
說你要是沒偷我的雞,我的兒子就今年死,要是你偷了我的
雞,你的兒子今年死。農(nóng)村吵架吵到一定份上,就是要賭咒,
才能結(jié)束。兩人信誓旦旦的。到了過年的時候,大年三十,
有個全球化的東西和一個小小的孤立的農(nóng)村聯(lián)系起來。那些
打工的人帶回來很多東西,都是全球化帶來的巫術(shù)一樣的東
西,那首歌也是這樣,Beyonce是一個全球化的符號。胡少
卿:哦,你有這方面的考慮。我讀的時候也想到了這個。阿
乙:其實(shí)農(nóng)村是這樣的,大家像聾子一樣活在現(xiàn)代社會。不
過,Beyonce,Ladygaga,包括鳳凰傳奇,都曾經(jīng)飄過。胡少
卿:現(xiàn)在真實(shí)的農(nóng)村就是這樣光怪陸離,一些外面來的很怪
異的東西,在農(nóng)村里的確存在。阿乙:這個故事我結(jié)了四次
牛B。你讀第一遍的時候覺得是個天作,第二遍是天作,第
三遍是神作,到第四遍的時候你就看出漏洞來了。漏洞在哪
兒呢?前面90%,他都是按照完全冷漠、冰冷的視角去寫的,
到結(jié)尾作者開始戀戰(zhàn),舍不得離開這么美好的故事,舍不得
結(jié)束它。他寫那些人來分尸,有的來鋸?fù)龋?/span>有的來開腸破肚, 有的拿走了心,有的拿走了肺。那段寫得特別油滑。讀了三 四遍之后,我覺得這個地方是一個作者不懂得控制結(jié)尾,不 懂得怎么離開,所以導(dǎo)致這個神作里有個很別扭的問題,就 是前面都很克制,后面就油滑了。而且有個合法性的問題, 就是一個農(nóng)婦怎么懂得遺體捐贈這一套東西,而且是代簽。 這個合理性不夠。戀戀不舍最容易帶來油滑,語言的油滑, 和那種自戀的東西。很多年以后,《兄弟》那部小說,他保 留的就是10%的這個油滑,90%的冷靜全部不見,這是很危 險的。我對自己很警惕。油滑是我看到的一個問題。每個作 者都是這樣,對自己稍有放縱,你的骯臟、自戀、丑態(tài)都會 關(guān)系,但你能感到背后這個作者的思想應(yīng)該是不錯的。但是 到《活著》的時候,你就看見他開始有意識地煽情,這說明 讀者和一些市場的反應(yīng)已經(jīng)在侵襲他了,已經(jīng)來找他了。最 開始來找他的都是世界名著,后來找他的可能都是讀者的意 見。《活著》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煽情。好多人說讀《活著》 的時候半夜起來哭。然后我就想,這個作品可能不行。因為 好多電視劇也是這樣,人也是被感動得要哭。《媽媽再愛我 一次》,哭得肯定比《活著》還多。到《許三觀賣血記》的 讀以后,你所閱讀的對象的價值觀就是你的價值觀,這個不 用分誰是誰的。人開始是沒有價值觀的,人只有在閱讀的過 程中、在接受外界的東西時才會形成價值觀。人就像一頭牛 一樣,始終要拿起鞭子鞭策自己去讀一些好東西,你讀蘇格 拉底,蘇格拉底的價值觀就是你的,你可以把他的一些你認(rèn) 為不對的東西拋棄掉,但是你每天晚上看《我是歌手》、看 《中國最強(qiáng)音》的話,你的價值觀就是章子怡的,很棒,很 棒,天天就是很棒;就是羅大佑的,羅大佑大家覺得有文化, 但是他真正有多大文化?胡少卿:你寫小說一直保持著形式 探索的熱情,在每篇小說里都嘗試新的寫法。你是怎么考慮 的?阿乙:我其實(shí)是設(shè)定了時間界線的。我從2006年開始 寫,允許自己寫到2011年,大概五年的時間,這五年里放 肆地去看,放肆地去閱讀,放肆地去模仿,放肆地去掌握別 人的技巧。比如加繆的,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很多技術(shù) 它本身也就完成了。我寫《春天》探索了一種形式:這個故 事是螺絲型的,第一節(jié)的第一句話,就是第二節(jié)的最后一句 話,永遠(yuǎn)可以這么讀下去,第二節(jié)的第一句話,就是第三節(jié) 的最后一句話。到最后,你從最后一章開始讀起,倒過來讀, 它又是一篇,而且符合你的線性結(jié)構(gòu)。我倒敘,還有不停地 頂針,讀起來就比較好玩,這是一個探索,倒過來寫,對尋 找一個很悲慘的女孩為什么死蠻有幫助。而如果你從開始寫 到她怎么死,這樣寫的話,反而可能有點(diǎn)怪。胡少卿:現(xiàn)在 比寫容易。差點(diǎn)寫病了。胡少卿:寫作很需要體力。記得殘 雪說過,她經(jīng)常每天要跑五千米鍛煉身體。阿乙:吐口水式 的寫作不需要體力,而我的這種寫作充滿了失敗。吐口水式 他就能泡出都市文學(xué)的好茶。好比張愛玲,她不是名門之后, 她怎么能寫出來呢?她寫著寫著可能就像夏衍一樣寫個包 身工。打多了麻將才知道打麻將有什么意思。胡少卿:在你 默默無聞的時候,你是如何保持寫作的沖動和熱情的?阿 乙:開始我對發(fā)表的環(huán)境是持有懷疑的,我覺得我這么寫的 話有誰能知道呢?別人介紹我是一個寫作的,我什么都沒發(fā) 表過,我很羞慚:“我不是我不是,我就是寫寫博客的。”我 當(dāng)時立下一個志愿,就是有可能終生就這么寫下去,給自己 留一堆,無所謂,反正有博客在那里留著。開始打擊我的人 就他一個是聰明的。他在寫人與人的隔閡與疏離的時候,完 全是鳥兒在空中飛,充滿嘲笑,嘲笑就是他的漏洞。像博爾 赫斯,每個作品何其精妙,但是他的漏洞就在于他的精妙, 就像魔術(shù),你在看完一個魔術(shù)的時候,覺得特別精妙,但是 你同時會想,這個魔術(shù)是沒有力量的。我讀完了一定要在崇 了,但是它會一直在那兒。讀你的那些生活小片段我感到, 在一般人眼中平面雜亂的現(xiàn)實(shí),到了小說家筆下,會變得很 生動,通過一種洞察力重新組織起來,好像透過表象,抓住 話,或者哪一個作家給另外一個作家寫信那種深入和透徹的 交流。你會發(fā)現(xiàn)世界上講文學(xué)的人各有各的道理,這個道理 大地震,我會感到悲痛,但他們的想法,他們的生活方式, 完全跟這些創(chuàng)作者沒有關(guān)系。文藝絕對不能俯就于大眾。文 藝就是提供一種有效活著的方式,哪怕最后只剩你自己在看 你自己的作品。胡少卿:你說的這些有效活著的人,既包括 你剛才說的為數(shù)不多的創(chuàng)造者,也包括能夠欣賞這些創(chuàng)造的 人,是嗎? 阿乙:我覺得包括那些向上的人。你在地鐵里,你就 看,每個人都像默哀一樣,拿著手機(jī),這一排都是。這批人 就是無效活著的人,你可以蔑視他們。胡少卿:如果他恰好 在手機(jī)上看你的小說呢?阿乙:很罕見,怎么可能呢。有幾 個人在地鐵上讀蘇珊·桑塔格,讀亞里士多德?當(dāng)然,我們 不能去胡亂評說另一個人活著的意義,每個人活著都有他的 價值所在。但你走上創(chuàng)作的道路以后,你就自然而然地不想 跟那些人打交道。設(shè)想那些人,假如臨去世之前留下什么遺 言,遺言可能是這樣的:我沒什么遺言可留,我就覺得相比 著燠熱。道路天橋編織起來,日光里像只爍白籠子。蟬影子 鳥影子一個不見。偶爾車過,一街的浮塵日影便喘息起來。 咖啡館里滿地暗暗的陰涼。一盞洛可可式黃吊燈,照著中午 的玻璃鏡。咯噔咯噔爬上木樓梯,滿眼茶幾軟椅盡是空蕩, 只左壁一個鴉青衣裳的女人,面目埋在電腦屏幕里,一味模 糊下去,倒像是她桌上那盞咖啡杯的背景。中間一個男子睡 著。紫粗布的沙發(fā)上,一團(tuán)亂發(fā)像楊樹上的鳥巢,棲止在扶 手上。又像秋野的飄蓬。茶幾上三兩個狼藉杯盤。再遠(yuǎn)些, 陽臺窗子半開,日光斜進(jìn)來。風(fēng)吹得縐紗簾子如清波漾漾。 這大屋真是暗啞油畫一張。我四下一望,看來阿乙還沒來。 空中仿佛浮有依依呀呀的電扇聲,瞌睡蟲四處飛。“阿乙!” 老師叫道。我一驚。木樓梯上并無人影。飄蓬升起來。一張 惺忪面目鋪展開來,滿是呵欠。呵欠里說:“你們到啦?” 這人真瘦。火紅T恤衫一穿,像個收攏來的燈籠骨,慵慵立 在面前。腳下趿一雙人字拖,磨過地面噠噠響。兩片雙眼皮, 羊角也似,抵牾這城市陰陰的馴化。說話只是粗闊,一點(diǎn)不 像文字的細(xì)密勁,其中一股子萬事無謂的坦蕩,野得很。我 一口齒的嚼字嚼句,立馬羞赧下去。又頹唐。存在主義的頹 唐,鋪成眼底迷蒙的火,四散開來,看這世間盡是荒誕面皮。 荒誕面皮的海里,浮出一個島,漫天的碧青碧翠,那便是純 文學(xué)。他眼底那團(tuán)微暗的火,咻地燃亮。簡直滔滔,那火與 言語。皮蘭德婁是個金子。巴里科,小資作家,一杯咖啡。 福克納的什么我都喜歡。《罪與罰》,牛氣。白煙飄得無稽無 涯。他斜坐在煙霧里,飄蓬熠熠,像枚萬壽無疆老神仙,蓬 想,畫名就叫“行走的現(xiàn)代派”。 刊載于《西湖》雜志2013 年第7期 阿乙:重拾“先鋒派”的激情 (2013-06-22 00:27:20)文 | 胡 少卿 阿乙在當(dāng)代文壇有點(diǎn)橫空出世的味道。2008年因微博 意見領(lǐng)袖王小山、羅永浩的推崇始漸為人知,并出版首部小 說集《灰故事》。此后保持平均每年一本的頻率,陸續(xù)出版 小說集《鳥看見我了》(2010年)、隨筆集《寡人》(2011年), 中篇《模范青年》(2012年),小長篇《下面,我該干些什么》 (2012年),小說集《春天在哪里》(2013年)。許多人初讀 阿乙會聯(lián)想到余華。不僅因為他的小說像早期余華一樣迷戀 暴力和冷漠,還因為他和余華有類似的生活軌跡:余華從海 鹽牙醫(yī)出發(fā),阿乙從瑞昌警察出發(fā),撥開艱難游向中心,才 華是唯一的通行證。2002年阿乙離開家鄉(xiāng)江西瑞昌,外出闖 世界。此前他在省內(nèi)讀警察專科學(xué)校,做過五年的小鎮(zhèn)警察 和公務(wù)員。對鄉(xiāng)鎮(zhèn)生活的反芻構(gòu)成了迄今為止他幾乎全部的 寫作題材。他的小說是一個賈樟柯電影式的世界,活躍著妓 女、逃犯、偷情老漢、打牌民警、臺球桌邊的青年、苦苦思 索的民間哲學(xué)家。他的故事可以總括為“一個鄉(xiāng)間警察的所 見所聞”,有論者稱他是把公安局的檔案柜搬到了小說里。 這決定了他的小說充滿懸念,使讀者獲得一種偵破和窺秘的 快感。作者像一個手持利刃的法醫(yī),劃開表皮,展示生活觸 目驚心的內(nèi)臟。閱讀快感,哪怕是一種殘酷的快感,是阿乙 小說追求的首要目標(biāo)。阿乙的文學(xué)趣味給人一種“純正”的 感覺。在浮出水面之前,他曾花費(fèi)多年苦讀卡夫卡、博爾赫 斯、加繆、福克納、皮蘭德婁、巴里科、余華等人的作品, 其飄忽殘酷的文字讓人聯(lián)想到殘雪《山上的小屋》、余華《河 邊的錯誤》,給人“先鋒派歸來”的錯覺。他自述喜歡把作 品當(dāng)做一件工藝品來打磨,渴望作品達(dá)到“沒有一句廢話” 的境界。他的語言簡潔,準(zhǔn)確,揭示出事物之間的神秘聯(lián)系。 臺灣作家駱以軍稱阿乙是“動詞占有者”。隨便拈出一個句 子:“打工的人慢慢歸來,在孩子們面前變化出會唱歌的紙、 黃金手機(jī)以及不會燃燒但是也會吸得冒煙的香煙,這些東西 修改了楊村。”(《楊村的一則咒語》)“變化”和“修改”用 得多好。阿乙還特別在意故事的敘述技巧、結(jié)構(gòu)方式,比如 《意外殺人事件》是一篇努力按照“非”字的幾何形狀結(jié)構(gòu) 的小說,講述六個人從六條小巷走出,在中間的大道上遭遇 同一種命運(yùn):死亡。在“先鋒派”退潮20年后,阿乙重拾 形式探索的激情與沖動,仍然令人尊敬。1980年代的“先鋒 派”小說往往模糊了時間和地點(diǎn),對現(xiàn)實(shí)政治進(jìn)行一種表面 上的疏離,以強(qiáng)化“純文學(xué)”之“純”。阿乙的不同之處是, 他把時間和地點(diǎn)明確化了,使小說與中國鄉(xiāng)村、城鎮(zhèn)在世紀(jì) 之交的真貌發(fā)生連接。形象點(diǎn)說(未必準(zhǔn)確),這相當(dāng)于把 早期余華和后期余華糅合在一起。在廣受贊譽(yù)的短篇《楊村 的一則咒語》中,村婦鐘永連懷疑鄰居吳海英偷了她的雞, 因此賭下殘酷的咒語:“好,要是你偷了,今年你的兒子死; 要是沒偷,今年我的兒子死。”第二天,雞自己回來了。故 事的結(jié)局是兩個兒子都從南方打工回來過年,吳海英的兒子 開著車帶著女友,鐘永連的兒子則疲憊地死在自家的床上, 打工地的工作環(huán)境摧毀了他的身體。這個故事里有一種堅硬 的宿命,它強(qiáng)調(diào)的不是咒語應(yīng)驗的偶然性,而是一個大時代 中帶有普遍性的悲劇。阿乙一直在追隨加繆于《西西弗的神 話》中提出的命題:如何度過荒謬的一生?《下面,我該干 些什么》把對這個命題的思考推到極致。小說里的“我”為 了讓空虛的時間變得充實(shí),不惜殺掉一個美好的女孩成為逃 犯。這部作品既有加繆《局外人》的冷漠,又有陀思妥耶夫 斯基《罪與罰》的緊張,它嘗試對作家的道德感進(jìn)行節(jié)制, 而只忠于寫作本身。當(dāng)西西弗開始認(rèn)清并正視自己的命運(yùn) 時,這同時意味著一種得救。我們也應(yīng)該這樣來理解阿乙小 說中的殘酷,正如阿乙所言:“人們只有對自己的內(nèi)心坦誠, 去認(rèn)清那些本就存在的結(jié)局、宿命,才會在絕望中清醒,才 能走上自我找尋的道路。”(《殺手阿乙》) 刊于《人民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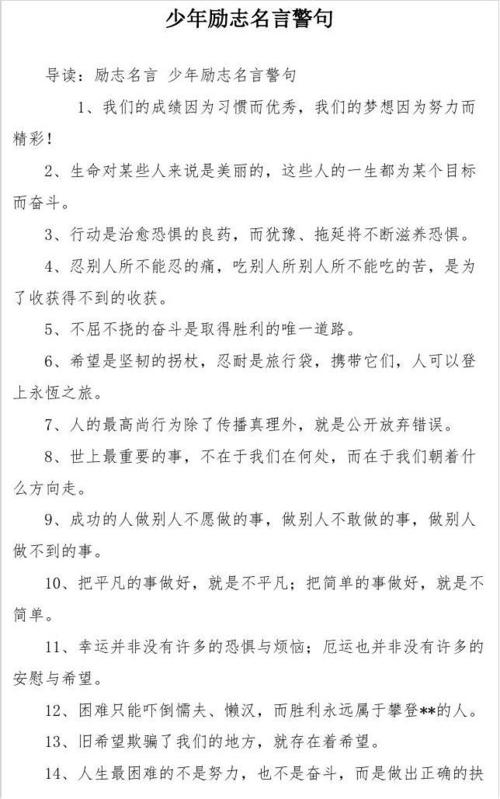
本文發(fā)布于:2023-11-28 11:21:45,感謝您對本站的認(rèn)可!
本文鏈接:http://www.newhan.cn/zhishi/a/1701141705228984.html
版權(quán)聲明:本站內(nèi)容均來自互聯(lián)網(wǎng),僅供演示用,請勿用于商業(yè)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權(quán)益請與我們聯(lián)系,我們將在24小時內(nèi)刪除。
本文word下載地址:阿乙訪談:好作家的爛作品給我信心.doc
本文 PDF 下載地址:阿乙訪談:好作家的爛作品給我信心.pdf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