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0日發(fā)(作者:郴字怎么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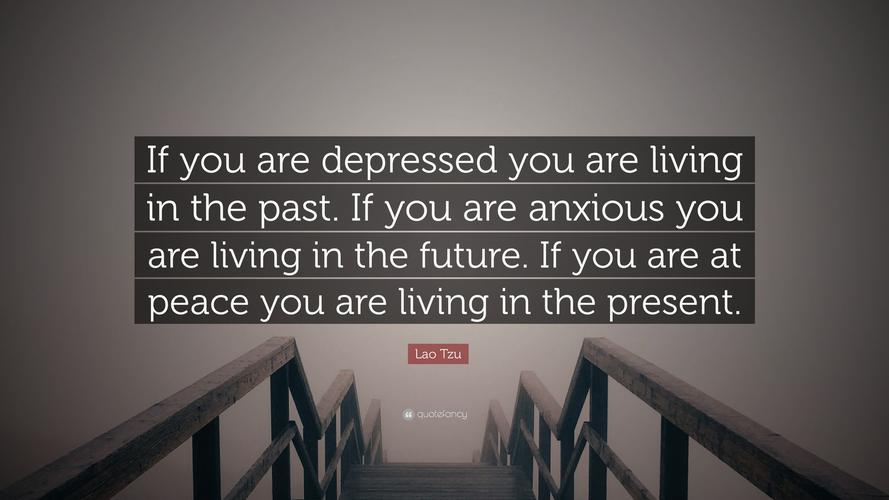
簡述《漢書.藝文志》的六種分類
《漢志·藝文志》是班固在劉歆《七略》的基礎(chǔ)上刪節(jié)其要而成,而《七略》又是在《別錄》的基礎(chǔ)上修訂而成的。《別錄》是漢成帝河平二年(前27)開始的我國歷史上最早、規(guī)模最大的整理群書的產(chǎn)物。這次整理群書,集中了當(dāng)時有代表性的一大批學(xué)者。《別錄》《七略》是這次校書的理論總結(jié),是集體智慧的產(chǎn)物,它比較系統(tǒng)地反映了當(dāng)時學(xué)術(shù)界對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看法。所以《漢志·藝文志》的文學(xué)思想,實(shí)際是西漢后期代表性的文學(xué)思想。
《漢志·藝文志》體現(xiàn)的文學(xué)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詩賦不同于經(jīng)學(xué),也與學(xué)術(shù)文章有別。從內(nèi)容上講,它是賢人失志、離讒憂國的情志抒發(fā);從體制上說,則以有韻為其特點(diǎn)。
《漢書·藝文志》把圖書分為六大類: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shù)術(shù)略、方技略,每略又分若干小類。“六藝”本來是先秦貴族教育的六門課,孔子講的“六藝”既是六門課,也是六種書。《六藝略》大致相當(dāng)于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基礎(chǔ)理論。《諸子略》從學(xué)術(shù)源淵和思想體系上來分,是對《莊子·天下篇》以來前人研究諸子百家的總結(jié)。《詩賦略》以文體來分類。《兵書略》、《數(shù)術(shù)略》、《方技略》則是以內(nèi)容和作用來分類的。
阮孝緒《七錄序》云:“《七略》‘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既多,所以別為一略。”章學(xué)誠亦本是說,他在《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中說:“詩賦本《詩經(jīng)》支系。”
現(xiàn)代學(xué)者多從其說。如余嘉錫先生《古書通例》就說:“以《七略》中史部附《春秋》之例推之,則詩賦本當(dāng)附入六藝詩家,故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其所以自為一略者,以其篇卷過多,嫌于末大于本,故不得已而析出。”但“六藝略”中的詩類,都是有關(guān)齊、魯、韓、毛四家詩的;四家說《詩》,主要立足點(diǎn)是“王者之教化”,“把《三百篇》作了政治課本”(聞一多《匡齋尺牘》之六)。如果把“詩賦略”并入“詩類”,不僅篇數(shù)多寡懸殊,有喧賓奪主之感,更嚴(yán)重的是內(nèi)容捍格難入。所以,“詩賦略”獨(dú)立一項(xiàng),這是基于對“詩賦”獨(dú)立特點(diǎn)認(rèn)識,它實(shí)際上反映了西漢人的文學(xué)觀念:文學(xué)既獨(dú)立于經(jīng)學(xué),也與其它學(xué)術(shù)性應(yīng)用性的文章有別。
“六藝”典籍的來源是官書舊典和貴族教育,這些書作者無定,一般只能有整理者。“諸子”則是私家著作。“六藝”談一般原理,“諸子”談一家之言,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學(xué)術(shù)。戰(zhàn)國后期,荀子、屈原等離讒憂國,吐為哀怨之詞。“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yáng)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漢書·藝文志》總序),與六藝諸子的區(qū)別更為明顯,文學(xué)類創(chuàng)作與學(xué)術(shù)類著作遂判然二別。這種分別的是從性質(zhì)上著眼的,不是從形式上入手的。清人劉天惠《海學(xué)堂初集》卷七《文筆考》說:
漢尚辭賦,所稱能文,必工于賦頌者也。《藝文志》先六經(jīng),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數(shù)術(shù),次方技。六經(jīng)謂之六藝,兵書、數(shù)術(shù)、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旨,雖有蔽短,合其要?dú)w,亦六經(jīng)支與流裔。”據(jù)此,則西京以經(jīng)與子為藝,詩賦為文矣。
劉師培《論文雜記》也對此有說明:“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經(jīng)諸子之中,非六經(jīng)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若詩賦諸體,則為古人有韻之文,源于古代之文言,故列于六藝九流之外,亦足證古人有韻之文,另為一體,不與他體相雜矣。”郭紹虞指出:“以前分詩文二類,是形式上韻散的分別,到劉歆、班固分出《詩賦略》一類,與《六藝略》《諸子略》并列,那就對于文學(xué)的性質(zhì),已經(jīng)有比較正確的認(rèn)識了。”[1]郭先生還舉了《漢書》中以文章之義稱“文”,以博學(xué)之義稱“學(xué)”的例證。
還要說明的是,西漢時“賦”所包含的作品種類,要比后世的賦包含的種類多。像《漢書·韋賢傳》所錄韋孟的《諷諫詩》、《在鄒詩》、韋玄成的《自劾詩》、《戒子孫詩》等,在《漢志》中應(yīng)當(dāng)歸于哪一類?這些詩在體制上同《詩經(jīng)》完全一樣,但卻不是說《詩》的,自然不能歸入“六藝略”的“詩”類;而一般人可能首先想到“歌詩”類,但這些詩顯然是不入樂的,歸入“歌詩”類,不合體例。我認(rèn)為,劉班是把它們歸入賦類的,因?yàn)樗鼈冸m然不能歌,但可以誦。《漢志》是將“誦詩”隸于賦類的。再比如,漢代有數(shù)量相當(dāng)多的“頌”,著名者有王褒的《圣主得賢臣頌》、《甘泉宮頌》,有班固的《竇將軍北征頌》,馬融的《廣成頌》、《東巡頌》、《南巡頌》等,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是典型的賦體。而東方朔的《旱頌》、王褒的《碧雞頌》則是調(diào)侃性質(zhì)的俗賦。其他像贊(如司馬相如的《荊軻贊》、劉向的《列女傳贊》)、銘(如東方朔的《寶甕銘》、劉向的《熏爐銘》、崔骃的《扇銘》、班固的《封燕然山銘》及眾多的鏡銘)、箴(如揚(yáng)雄的《十二州箴》《上林苑令箴》《酒箴》、崔瑗《東觀箴》《灌堤謁者箴》、崔琦《外戚箴》)等,都是歸入賦類的。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辨詩》曰:“其他有韻之文,漢世未具,亦容附于賦錄。”
第二,詩賦分類是由于傳播方式的不同。
《詩賦略》分五家,第一家為屈原賦,下隸賦家20人,賦361篇;第二家為陸賈賦,下隸賦家21人,賦274篇;第三類荀卿賦,下隸賦家25人,賦136篇;第四類雜賦12家,賦233篇。第五家為歌詩類,下隸28家,詩34篇。前三家按時間先后分列賦家姓名和作品數(shù)目,雜賦類以作品題材及體制為序,無作者姓名。歌詩類作品也以無作者姓名者居多。
這個分類是兩個不同的層次。前四家為“賦類”,后一家是“歌詩類”,這是第一層次。第二層次才是將賦分為四家。但是第一層和第二層又有交叉現(xiàn)象:前三家是文人創(chuàng)作,是口誦文學(xué)的書面化,“雜賦”和“歌詩”更具有口誦文學(xué)的性質(zhì),“雜賦”最后的“成相雜辭”“隱書”更為接近“歌詩”;文人賦——雜賦——歌詩,這是一個 “誦唱”因素漸次強(qiáng)化的過程。
《詩賦略敘》說:“傳曰:‘不歌而頌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這是對賦的特點(diǎn)的說明,也是《漢志》判斷賦的標(biāo)準(zhǔn)。“傳曰”云云,只不過表示有所本且本于儒學(xué)而已。“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fēng),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亦可以觀風(fēng)俗,知薄厚云”,這是對詩的特點(diǎn)的說明。很清楚,劉、班所謂詩賦,主要就其傳播方式來把握:賦“誦”而詩“歌”。正如章太炎先生《國故論衡·文學(xué)總略》說:“不歌而誦,故謂之賦;葉于簫管,故謂之詩。”文學(xué)是語言藝術(shù),文學(xué)語言是有別于日常語言的音樂化的“樂語”。文學(xué)是在同音樂相分離的過程中獨(dú)立出來的,詩賦便是這種獨(dú)立的標(biāo)志。“樂語”最基本的方式是歌唱和講誦。歌唱對于語言簡明性的要求,講誦對于語言華麗性的要求,使傳播方式的區(qū)別轉(zhuǎn)化為表達(dá)方式和文體的區(qū)別,于是就有了詩和賦這兩種不同的文體。
第三,抒發(fā)感情與描繪客觀事物是詩賦的主要職責(zé)。
按照《漢志》的體例,六略前有總敘,所別每類之后又有小敘,我們可以通過這些敘例來了解劉、班分類的標(biāo)準(zhǔn)及其思想。但《詩賦略》僅有總敘而無小敘。這給我們探求劉、班的文學(xué)思想造成了很大困難。
章學(xué)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云:“《漢志》分藝文為六略,每略又各別為數(shù)種,每種始敘列為諸家,猶如《太玄》之經(jīng),方州部家,大綱細(xì)目,互相維系,法至善也。每略又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qū)為五種,而每種之后,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遺邪?抑流傳之脫簡邪?”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條理》則認(rèn)為《詩賦略》本無敘例,他說:“詩賦各分以體,無大義例,故《錄》《略》不為小序,而班氏因之,不盡由于疏漏也。”不管由于佚失還是本來就沒有寫成,而《詩賦略》的分類依據(jù)卻成了許多學(xué)人討論的課題。
章學(xué)誠認(rèn)為《漢志》所列諸賦,各有宗旨,前三類為一個標(biāo)準(zhǔn),可比擬諸子。雜賦為一標(biāo)準(zhǔn),為總集之類(此本胡應(yīng)麟說)。姚振宗基本同意章學(xué)誠之說,他說:“《詩賦略》舊目凡五,一、二、三皆曰賦,蓋以體分。四曰雜賦,五曰歌詩,其中頗有類乎總集,亦有似乎別集。”劉師培從文學(xué)表達(dá)方式上分析三類賦的特點(diǎn),認(rèn)為前三類分別是寫懷之賦、騁辭之賦、闡理之賦。章炳麟的說法與劉氏相近,認(rèn)為屈原賦言情,孫卿賦效物,陸賈賦是縱橫之變[2]。章學(xué)誠認(rèn)為所列賦家,各有宗旨,卻未能進(jìn)一步深究其宗旨所在,而且下文以“不可考”概括之,則說明其宗旨也難以深究。劉師培和章太炎從表述方式上分,抓住了文學(xué)不同于諸子的特點(diǎn)。過去探討古代文學(xué)思想,從古代的文學(xué)理論方面探討的多,而
從古代的文學(xué)作品挖掘的較少。劉師培和章太炎能從漢賦本身的特點(diǎn)分析劉、班詩賦分類的理論,因而很有啟發(fā)意義。
詩賦的抒情性,從屈原《九章·惜誦》“惜誦以致愍兮,發(fā)憤以抒情”以來,文人多有論及。司馬遷在劉安《離騷傳》基礎(chǔ)上改編而成的《屈原傳》說:“‘離騷’者,猶離憂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有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離騷就是抒發(fā)憂愁。漢代諸多楚辭體賦作,都是以屈原口吻抒發(fā)憂愁幽思。王褒《洞簫賦》寫道:“憤伊郁而酷□,愍眸子之喪精;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fā)憤乎音聲。”劉向《九嘆》也寫道:“遭紛逢兇,蹇離尤兮。垂文揚(yáng)采,遺將來兮。……外彷徨而游覽兮,內(nèi)惻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原假簧以舒憂兮,志紆郁其難釋。嘆《離騷》以揚(yáng)意兮,猶未殫於《九章》。”論者或以為是模仿屈原的口氣的無病呻吟。但是如果我們結(jié)合這些賦家的身世遭遇,就會覺得大多數(shù)作品未必如此。劉歆在《七略》里明確總結(jié):“詩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
至于賦的描寫特征,從司馬相如“賦跡”、“賦心”的理論,直到班固的《兩都賦序》都有很好的說明,這是當(dāng)時學(xué)人的共識。
第四,關(guān)心國是、干預(yù)政治是對賦進(jìn)行價值判斷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
從表現(xiàn)手法上分析《漢書·藝文志》賦的分類思想,自然有其道理。但如果用此標(biāo)準(zhǔn)具體分析各類賦作,就會發(fā)現(xiàn)很多捍格難通處。因?yàn)榧词雇蛔骷业淖髌罚部梢杂胁煌捏w裁和表達(dá)方式。如揚(yáng)雄之《反離騷》、《廣騷》、《畔牢騷》三篇,今皆在本傳,乃抒
情者,而《漢志》歸入“騁辭賦”類;屈原有《橘頌》、王褒有《洞簫賦》,皆效物者也,而《漢志》歸入“言情類”。 馮商有《鐙賦》,亦“效物者”,而歸入“騁辭類”;司馬遷有《悲士不遇賦》,本抒情者也,而《漢志》歸入“騁辭類”。枚皋實(shí)滑稽之雄,其賦嫚?wèi)虿豢勺x,而歸入騁辭之陸賈賦,也不恰當(dāng)。《詩賦略》并不是嚴(yán)格意義上的文體分類,而是以人為綱的分類。由于每一個作家的創(chuàng)作往往使用多種文體和多種表現(xiàn)手法,所以以人為綱的分類本身就存在文體上和表現(xiàn)手法上的相互交錯現(xiàn)象。那么,《詩賦略》賦分四家,應(yīng)當(dāng)還體現(xiàn)劉、班另外的文學(xué)思想。
漢人對賦的價值的評說,集中在“諷諫”這一點(diǎn)上。司馬遷以“風(fēng)諫”評判司馬相如賦的價值,揚(yáng)雄把賦分為“詩人之賦”和“詞人之賦”,他說:“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3]。所謂“則”,就是有“諷諫”的作用。劉向把屈原賦、荀況賦與《詩經(jīng)》相比較,充分肯定其諷諭之義的價值,并批評司馬相如、揚(yáng)雄的賦“沒其諷諭之義”。班固的《兩都賦序》明確提出賦的使命和價值就是對政治得失進(jìn)行頌揚(yáng)或諷諭,所謂“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進(jìn)忠孝”,“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總之,漢代賦論家或者就賦有無諷諫用意而判斷它的價值,或者就讀者沒有接受諷諫而指責(zé)漢賦沒有諷諫效果,從而懷疑漢賦的價值。
漢代人不僅以“諷諫”作為評賦的標(biāo)準(zhǔn),而且當(dāng)作寫賦的準(zhǔn)則,這一點(diǎn)我們可以從《漢志》中賦家在諸子中的類屬得到證明。《漢書·藝文志》中,漢代人在“詩賦略”列名,又在“諸子略”列名的,共有十家;這十家中,列名儒家的有九家,列名雜家的一家。范曄《后漢書》沒有《藝文志》,清人錢大昭、侯康、顧櫰三、姚振宗、曾樸五家有《補(bǔ)后漢書藝文志》,但他們的補(bǔ)志是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沒有賦家專略。我們按照嚴(yán)可均《全
后漢文》,將留有賦作的人,對照《補(bǔ)志》(以姚振宗所著為主)子部,其中有19人留有賦且在子部有名,這19人中,屬于儒家者有16人之多。漢代賦家?guī)缀踅匀肴寮遥f明當(dāng)時賦家作賦確實(shí)是以儒家的諷諭思想為主導(dǎo)的,這一點(diǎn)與漢代人對賦的評論標(biāo)準(zhǔn)是一致的。
所以,漢代學(xué)術(shù)界創(chuàng)作賦、評價賦的主要標(biāo)準(zhǔn)是“諷諭”,那么作為集當(dāng)時學(xué)術(shù)思想之大成的《七略》和《漢志》把賦分為四類,其標(biāo)準(zhǔn)也當(dāng)與之相通。
“《國風(fēng)》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正因?yàn)榍霓o賦體兼風(fēng)雅,骨含諷諫,故《七略》列屈原賦為第一。屈原賦以下二十家,大概是《楚辭》的雛形。考《楚辭章句》所錄凡屈原、宋玉、景差、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yán)忌、王褒、劉向九家,今《漢志》屈原賦二十家中不見景差、東方朔,其馀七家皆有之。當(dāng)然《漢志》以人為綱,凡此人的賦作,全部著錄,而《楚辭》則為別裁精選,故只能說“屈原賦”類是《楚辭》的雛形。姚振宗《漢志拾補(bǔ)》認(rèn)為屈原賦類“二十種大抵皆楚騷之體,師范屈宋者也,故區(qū)分為第一篇”,大概也是這個意思。
《漢志》列“陸賈賦”以下二十一家賦為第二類。這二十一家中,只有揚(yáng)雄的賦保存了下來,其馀都散佚不傳。揚(yáng)雄的賦,尤其是《七略》所錄的四篇[4],模仿同鄉(xiāng)司馬相如的賦作,靡麗之賦,勸百諷一,馳鄭衛(wèi)之聲,曲終奏雅,《詩》人之諷諫之旨陵遲式微。所以他晚年很后誨,輟不復(fù)為。
這類賦以陸賈為首,陸賈的賦雖然沒有傳下來,但據(jù)《史記·陸賈傳》,陸氏本為縱橫策士。建國后,他曾兩使南越,俱為太中大夫。《文心雕龍·才略》:“漢室陸賈,首發(fā)奇采,賦孟春而選典誥,其辯之富矣。”是陸賈賦以“辯富”著稱。劉師培《論文雜記》云:“陸賈為說客,為縱橫家之流,則其賦必為騁詞之賦。”從今存《新語》十二篇看,陸賈文章,概具賦體,如第七篇《資質(zhì)》的首段,敷衍鋪陳,引喻譬況,如不通觀全篇,極易疑其為寫物之賦。所以王利器說:“陸賈賦今不可得見矣,讀《新語》之文,不翅嘗鼎一臠矣。”[5]
這類賦家中的朱建、枚皋、嚴(yán)助、朱買臣等,皆工于言語,這些縱橫口便之人,在漢代大一統(tǒng)的新形勢下,與時俱進(jìn),棄其所長,投合君王的趣味,將以前游說君王的政論,改為聳動君王的文辭;將侈陳形勢的口論,變?yōu)殇伈蓳の牡馁x篇。“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fēng)諭之義”,于是風(fēng)諫之旨日益稀矣。
《詩賦略敘》說:“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fēng),咸有惻隱古詩之義。”是則劉、班以為荀、屈賦在有惻隱之義這點(diǎn)上是相同的,那么何以分而為二呢?荀卿賦以下25家,除荀子賦外,其馀皆亡。而荀子的這些賦篇[6],《佹詩》與屈賦相近外,其馀諸篇,格調(diào)迥異。究其內(nèi)容,基本上是儒家言,訓(xùn)戒的意味很濃,風(fēng)格頗類古代的箴銘,其中所缺乏的正是屈賦中那種澎湃激情。屈子言情,荀賦效物闡理。
雜賦一類,共錄12家233篇賦作,但不幸的是,沒有一篇保存下來。綜合前人的研究,這類賦,來自下層,篇幅纖小,作者無征,多詼諧調(diào)侃之意[7]。
《詩賦略》分賦為四家,內(nèi)容上以《詩經(jīng)》為對照物,看其“諷諫”教化之旨的多少。“屈原賦”是劉向編輯的《楚辭》的雛形,這類賦體兼風(fēng)雅,骨含諷諫,《詩》人風(fēng)諫之旨最濃。“陸賈賦”勸百諷一,競為侈麗閎衍之詞,《詩》人之諷諫之旨陵遲式微矣。“荀卿賦”直陳政教之得失,雖有惻隱諷諫的古詩之義,但與屈原類譬喻象征的方式不同,故得另為一類。《雜賦》一類,《詩》人之諷諫之義微乎其微。
最后要說明的是,近若干年來,一些學(xué)者強(qiáng)調(diào):所謂文學(xué)思想,主要是在文學(xué)理論或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對自我生命意識的一種感悟。而自我生命意識,主要是脫離政教的個人情感。我認(rèn)為,這種認(rèn)識是對中國文學(xué)傳統(tǒng)和傳統(tǒng)文學(xué)精神的否定。因?yàn)橹袊膶W(xué)中的風(fēng)諫傳統(tǒng),說到底就是一種憂國憂民的歷史責(zé)任感。關(guān)于中國文學(xué)的自覺時期,學(xué)術(shù)界至少有三種說法:一是魏晉說,二是西漢說,三為先秦說[8]。我認(rèn)為,不管是哪個時期自覺的,但以為自覺了的“文學(xué)”就是“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9],就是拋棄政教內(nèi)容,都是不符合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實(shí)際的。文學(xué)一旦獲得獨(dú)立主體的地位后,政教仍是其主要內(nèi)容,甚至是主要內(nèi)容。
注:
[1]郭紹虞《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頁。
[2] 章學(xué)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略第十五》:“古之賦家者流,……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shí)能自成一子之學(xué),與夫?qū)iT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敘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shù)十,少僅一篇,列于文林,義不多讓,為此志也。然則三種(按指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為家,而當(dāng)時之不能盡歸一例耳。”“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后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為篇,后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為篇,后世總集之體也。”以前三類為一標(biāo)準(zhǔn),后一類為另一標(biāo)
準(zhǔn)。在《文史通義·詩教下》中,他重申說:“賦家者流,猶有諸子之遺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詩賦之流,拘于文而無其質(zhì),茫然不可辨其流別也。是以劉、班詩賦一略,區(qū)分五類,而屈原、陸賈、荀卿定為三家之學(xué)也。”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bǔ)》論屈原賦類說:“此二十種大抵皆楚騷之體,師范屈宋者也,故區(qū)為第一篇。”論陸賈賦類說:“此二十一家大抵不盡為騷體,觀揚(yáng)子云諸賦,略可知矣,故區(qū)為第二篇。”論孫卿賦類說:“此二十五家大抵皆賦之纖小者,觀孫卿《禮》《知》《云》《蠶》《箴》五賦,其體類從可知矣。故區(qū)為第三篇。”論客主賦類說:“此十二家大抵皆尤其纖小者,故其大篇標(biāo)曰《大雜賦》,而《成相辭》、《隱書》置之末簡,其例亦從可知矣。”
劉師培《論文雜記》云:“自吾觀之,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皆漢代之總集類也,馀則皆為分集。而分集之賦,復(fù)分三類:有寫懷之賦,有騁辭之賦,有闡理之賦。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騁辭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闡理之賦,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寫懷之賦,其源出于《詩經(jīng)》;騁辭之賦,其源出于縱橫家;闡理之賦,其源出于儒道兩家。”
章炳麟《國故論衡·辯詩》:“《七略》次賦為四家,一曰屈原賦,二曰陸賈賦,三曰孫卿賦,四曰雜賦。屈原言情,孫卿效物,陸賈賦不可見,其屬有朱建、嚴(yán)助、朱買臣諸家,蓋縱橫之變也。”
[3] 見《法言·吾子》。時下的文學(xué)批評論著多認(rèn)為揚(yáng)雄所說的“詩人之賦”是指屈原等的作品,“詞人之賦”是指司馬相如等的賦作,恐怕有問題。揚(yáng)雄在同篇中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明確表示司馬相如的賦作是“麗以則”的。我以為,揚(yáng)雄所說的“詩人之賦”大致相當(dāng)于《詩賦略》中前三類賦,“詞人之賦”大致相當(dāng)于《詩賦略》中的“雜賦”。揚(yáng)雄說:“或問:景差、唐勒、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
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或據(jù)此認(rèn)為景差等人的賦是“詞人之賦”,但“必也淫”一句是有問題的,汪榮寶《法言義疏》已有詳細(xì)辨證;于省吾先生《雙劍誃諸子新證·法言新證》曰:“此文本作‘必也淫二則二奈何’。應(yīng)讀作:‘必也淫、則,淫、則奈何?’下‘淫則’下承上‘淫則’而言。上‘則’字即涉重文而脫。”據(jù)此,則揚(yáng)雄認(rèn)為景差等人的賦是雖有淫詞但尚有法則,即存諷諫之義。
[4] 《詩賦略》著錄“揚(yáng)雄賦十二篇”,最后“左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下班氏注云:“入揚(yáng)雄八篇”。顧實(shí)說:“蓋《七略》據(jù)雄傳,言作四賦,止收《甘泉賦》、《河?xùn)|賦》、《校獵賦》、《長楊賦》四篇,班氏更益八篇,故云十二篇也。其八篇,則本傳《反離騷》、《廣騷》、《畔牢騷》三篇,《古文苑》《蜀都賦》、《太玄賦》、《逐貧賦》三篇,又有《覈靈賦》、《都酒賦》二篇,凡八篇。”
[5] 王利器《新語校注》中華書局1996年“新編諸子集成”版第107頁。
[6] 《詩賦略》著錄“孫卿賦十篇”,顧實(shí)說:“十篇蓋十一篇之誤。《荀子》有《賦篇》、《成相篇》,成相亦賦之流也。《賦篇》有《禮》、《知》、《云》、《蠶》、《箴》五賦,又有《佹詩》一篇,凡六篇。《成相篇》分五篇,合《賦篇》之六篇,實(shí)十一篇。”按,《成相篇》的分章,古來就有不同意見,或分三章,或分四章,顧氏本王先謙《荀子集解》之說,分為五篇,以足《漢志》十篇之?dāng)?shù),并以為《漢志》“十”為“十一”之誤,此亦臆說者,難以令人信服。但荀賦的主要內(nèi)容如顧氏所述,則是可信的。
[7] 參見拙作《<漢書·藝文志>“雜賦”臆說》(《文學(xué)遺產(chǎn)》2002年6期)、《<漢書·藝文志>“雜賦”考》(《文獻(xiàn)》2003年2期)
[8] 日本學(xué)者鈴木虎雄于1920年在日本雜志《藝文》上發(fā)表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xué)論》中說“魏代是中國文學(xué)的自覺期。” 1927年,魯迅在《魏晉風(fēng)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中說:“用近代的文學(xué)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xué)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
所說是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一派。”康金聲《漢賦縱橫》(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說:“漢賦是文學(xué)自覺的第一聲春雷。”張少康《論文學(xué)的獨(dú)立和自覺非自魏晉始》(《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1996年2期)說:“文學(xué)的獨(dú)立和自覺是從戰(zhàn)國后期《楚辭》的創(chuàng)作開始初露端倪”,“到西漢中期就已經(jīng)很明確了”。趙逵夫先生《拭目重觀,氣象壯闊》(《福建師大學(xué)報》2003年第4期)中指出:“我認(rèn)為中國文學(xué)的自覺是在先秦時代。從創(chuàng)作方面來說,這種自覺從西周末年召伯虎、尹吉甫等人的創(chuàng)作已經(jīng)開始。綜合地來看,到屈原時代,無論在創(chuàng)作上還是理論上,還是文本意識上,都已經(jīng)達(dá)到自覺。”
[9]魯迅文章多次提到“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觀點(diǎn),全都是持批評的態(tài)度或諷刺的語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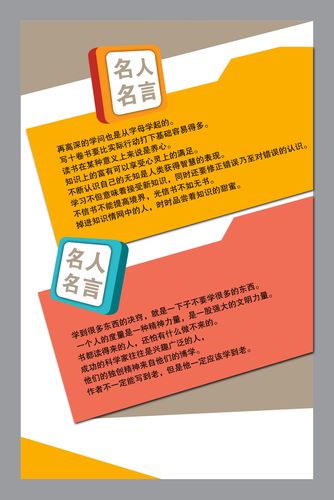
本文發(fā)布于:2024-02-20 14:46:59,感謝您對本站的認(rèn)可!
本文鏈接:http://www.newhan.cn/zhishi/a/1708411619145482.html
版權(quán)聲明:本站內(nèi)容均來自互聯(lián)網(wǎng),僅供演示用,請勿用于商業(yè)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權(quán)益請與我們聯(lián)系,我們將在24小時內(nèi)刪除。
本文word下載地址:簡述《漢書.藝文志》的六種分類.doc
本文 PDF 下載地址:簡述《漢書.藝文志》的六種分類.pdf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