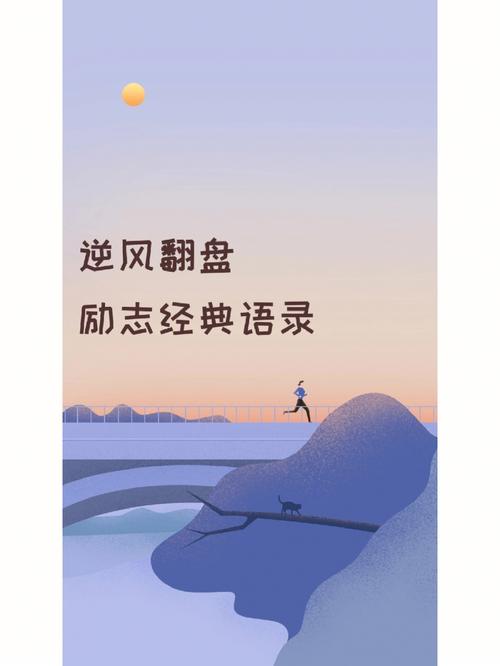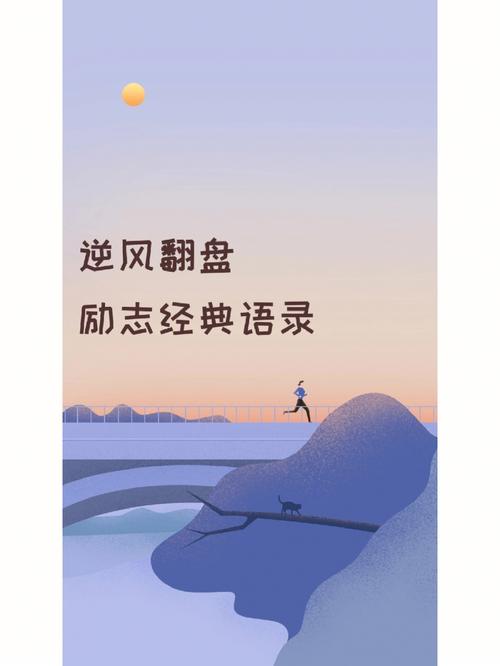
《文心雕龍》“風清骨峻”說
【內容提要】
劉勰提出的“風骨”說由于它的重要意義引起學界探討的熱情。本文在評說十種不同解說的基礎上,力圖按劉勰《風骨》篇原有的邏輯思路,提出新的解說,以接近劉勰的原旨。劉勰的《風骨》篇是從內質美的角度,對“情”與“辭”作出了規定。文章有“情”、“辭”兩大元素。“風清”是對“情”的內質美的規定,“骨峻”是對“辭”的內質美的規定。“氣”作為生理的力是生成“風骨”的力量。“風骨”與“采”對舉,則“風骨”是內質美,“采”的修飾是外形美。“風骨”作為劉勰所追求的藝術至境呼喚內質美與外形美的統一。
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中“風骨”的概念,從文學批評理論的角度看,為劉勰首創。這一概念既總結了漢魏以來文學的發展的經驗,特別是“建安風骨”創造的藝術經驗,同時又直接萌發了初唐陳子昂所呼喚的“漢魏風骨”,對后來剛健、爽朗、生動的“盛唐之音”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自此以后“風骨”成為中國文論的重要范疇。“風骨”問題的重要意義,使后來的學者對《文心雕龍?風骨》篇中“風骨”的內涵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見解,眾說蜂起,莫衷一是,迄今學術界尚未形成一致的意見。本文旨在清理眾說的基礎上,吸收眾說之長,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解說“風骨”,力圖接近劉勰“風骨”論的原旨。
一、關于“風骨”內涵的十種不同解說
學術界對劉勰《文心雕龍?風骨》有許多不同的解說,歸納起來大概有十幾種說法,但影響較大的有以下十種:
第一種,“風意骨辭”說。認為“風”是指文意的特點,“骨”是指文辭的特點。持此說者甚多。如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風骨“二者皆假于物以為喻。文之有意,所以宣達思理,綱維全篇,譬之于物,則猶風也。文之有辭,所以攄寫中懷,顯明條貫,譬之于物,則猶骨也。必知風即文意,骨即文辭……”又,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也說:“風即文意,骨即文辭,黃先生論之詳矣。”這是比較有權威的一說。此說的擁護者甚多。但反對的人也很多。有些論者死死抓住黃侃“風即文意,骨即文辭”這八個字不放,不顧黃侃先生的解說全文,認為黃先生把“風”和“文意”等同起來,把“骨”和“文辭”等同起來,是犯了“常識性”錯誤。實際上,把黃侃的解說簡單歸結為那八個字,是不夠客觀的。黃侃的解說中還有“風緣情顯,辭緣骨立”,“結言之端直者,即文骨也”,“意氣之駿爽者,即文風也”,“辭精則文骨成,情顯則文風生”等等(注: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99、第100頁。),結合這些解說我們可以看到黃侃并沒有把“風”與“文意”、“骨”與“文辭”簡單地等同起來。黃
侃所認為的“風”屬于“文意”方面的問題,“骨”屬于“文辭”方面的問題的看法,是從原作出發所得出的結論,肯定是有合理的方面的。
第二種,“情志事義”說。認為“‘風’是情志,‘骨’是‘事義’,兩者都是文學內容的范疇”,更具體說,“‘風’是作家發自深心的、集中充沛的、合乎儒家道德規范的情感和意志在文章中的表現”。“骨”指“事義”,“就是表現文章主題思想的一切材料觀點邏輯的內容”(注:廖仲安、 劉國盈:《釋“風骨”》, 原載《文學評論》1962年第一期,收入《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下,齊魯書社,1988年,第611―612頁。)。這種解說,在“風”的解釋上并無多少新意,但把“骨”解釋為“事義”就顯得很新鮮。這種說法源于較早的劉永濟先生的《文心雕龍校釋》一書。劉先生和此說的論者主要根據是《文心雕龍?附會》篇的一段話:
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
他們認為這段話是對于文章體制最完整、最全面的比喻,這里明明說“事義為骨髓”,所以《風骨》篇的“骨”指“事義”是確定無疑的。此說論者振振有詞,認為自己找到了“確證”,是推不翻的。但是問題在于主要不從《風骨》篇內找正面的證明,轉而從別的篇找旁證,這樣做是不是得當?是值得商榷的。
第三種,“風格”說。認為“風骨”是一種特殊的“風格”。此說也出現得比較早。據羅常培記錄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劉師培在《論文章有生死之別》的講題中說:“剛者以風格勁氣為上,柔以隱秀為勝。凡偏于剛而無勁氣風格,偏于柔而不能隱秀者皆死也。”劉師培的意思是,“風骨”與“隱秀”是兩種對立的風格,一偏于剛,一偏于柔。羅根澤說:“蓋風格雖非字句,而所以表現風格的仍是字句,所以欲求風格之好,須賴‘捶字堅而難多,結響凝而不滯’。風骨是文字以內的風格,至文字而外或者說是溢于文字的風格,劉勰特別提倡隱秀。”(注: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234 頁。)持“風格”說的還有馬茂元、吳調公和詹?}(注:馬茂元:《說風骨》,見《文匯報》1961年7月12日。吳調公:《劉勰的風格》,見《光明日報》1961年8月13日。詹?}:《文心雕龍的風格學》,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近期還有這樣的說法:《體性》篇是風格的通論,《風骨》篇是風格的專論。或者認為“風骨”只是對《體性》篇的個別句子的進一步發揮。如王運熙說:“風是指文章中思想感情表現得鮮明爽朗,骨是指作品的語言質樸而勁健有力,風骨合起來,是指作品具有明朗剛健的藝術風格。”(注:王運熙:《從〈文心雕龍?風骨〉談到建安風骨》,原載《文史》第九期,收入《〈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下,第641頁。 )又劉禹昌說:“繼《體性》篇歸納為八種藝術風格之后,又提出這種在他心目中認為最理想的標準藝術風格……大致相當于后世批評家所說‘陽剛之美’的藝術風格。
”(注:劉禹昌:《文心雕龍選擇?風骨》,《長春》,1963年第1期。)這意思是說, 在《體性》八體之外,還有“壯美”這一種風格。這一解說,的確是一種新解,有相當的道理,也很有意義。但也有值得懷疑的地方,統觀劉勰全書的結構,劉勰講“風骨”似乎不是要補充《體性》論的不足。如果脫離開《風骨》篇原文來評價上述觀點,未嘗沒有道理,但《體性》篇已把有關風格的各方面的問題講得很全面,連風格的“八體”也作了區分,劉勰似沒有必要用另一篇來補充它。《風骨》篇是獨立的一篇,有其獨特性,而且不但“壯美”、“陽剛”的風格要求有“風骨”,“優美”、“陰柔”的風格也要求有“風骨”,“風骨”似乎是對詩文的一種普遍的要求。
第四種,“剛柔之氣”說。認為“風骨”就是“氣”。此說最早見于清代,黃叔琳在《風骨》篇論“氣”的一段加眉批曰:“氣即風骨之本”,紀昀似不同意黃氏批語,另加批曰:“氣即風骨,更無本末;此評未是。”近人徐復觀同意并發揮了這一解說,他說:“所謂風骨,乃是氣在文章中兩種不同的作用;及由兩種不同的作用所形成的文章中兩種不同的藝術形相,亦即是所謂文體。”又說:“《風骨篇》之所謂風骨,依然是指的是作者的生理地生命力――氣,灌注于作品之上,所形成的兩種不同的形相。所以就兩種不同的生理地生命力而言,便可以說‘氣即風骨’。就文章兩種不同的形相而言,也可以說‘氣是風骨之本’,所以我
說紀昀兩句評語皆可成立。”(注:徐復觀:《中國文學中的“氣”問題――〈文心雕龍風骨篇〉疏補》,見《中國文學論集》,(臺灣)學生書局,第304、第310頁、第304頁、第310頁。)徐復觀的說法似有誤,他引的兩句評語,不是紀昀一人的評語,是黃氏和紀氏兩人的評語。但徐復觀要表達的意思是,人的氣有剛與柔不同的分別,剛氣灌注于作品之中,其表現就是“骨”,柔氣灌注于作品中,其表現就是“風”。的確,“氣”是《風骨》篇中一個重要的概念,從“氣”這個角度切入來疏解“風骨”,可以說別開生面,使我們對“風骨”問題的理解深化了一步,特別是“氣是風骨之本”的說法,我以為是切中肯綮的。這一點我在下面還要談到。但是,“氣即風骨”的提法,在氣與風骨之間劃了一個等號,似乎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這二者相等的話,劉勰已有《養氣》篇,集中論述了氣的問題,《風骨》篇豈不是重復了嗎?或許會說,這是層次的不同,那么人們就要問我們究竟在哪個層次上把風骨和氣相提并論呢?
第五種,“情感思想”說。認為“風”是情的因素,“骨”是理的因素,“風骨”是情感思想的表現。提出此說的是宗白華教授。他說:“我認為‘骨’是和詞有關系的。但詞是有概念內容的。詞清楚了,它所表現的現實形象或對于形象的思想也清楚了。‘結言端直’,就是一句話要明白正確,不是歪曲,不是詭辯。這種正確的表達就產生了文骨。但光有骨還不夠,還
必須從邏輯性走到藝術性,才能感動人,所以‘骨’之外還有‘風’。‘風’可以動人,‘風’是從情感中來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既重視思想――表現為‘骨’,又重視情感――表現為‘風’。一篇有骨有風的文章就是好文章。這同歌唱藝術中講究‘咬字行腔’一樣。咬字是骨,即結言端直,行腔是風,即意氣駿爽,動人情感。”(注: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48頁。)宗白華對“風骨”的解說,也很有新意。他從情與理的視角來說明風骨的不同及其聯系,確能自圓其說。對風的解釋更符合劉勰的原義,也更具有啟發性。但對“骨”的解釋,宗白華把“結言端直”(“一句話要明白正確”)直接與“邏輯性”相聯系,也似乎有些勉強。
第六種,“感染力”說。認為“風”是作品的“感染力”,馬茂元說:“風能動物,猶文章之能感動人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風便是文學作品的感染力。”風骨的特征“在于明朗、健康、遒勁而有力”(注:馬茂元:《說風骨》,《文匯報》1962年7月12日。)。持此說者不止此一人。這種說法就作品“風骨”所引起的藝術功效來說是有道理的。但致命的弱點是離開劉勰《風骨》篇的論述,對“風骨”本身缺少詳盡的說明,只是從“風”的字義上著眼進行解釋,是很不夠的。
第七種,“精神風貌美”說。認為“風骨”是“精神風貌美”,張少康說:“我們認為,把風骨理
解為文學作品中的精神風貌美,風側重于指作家主觀的感情、氣質特征在作品中的體現;骨側重于指作品客觀內容所表現的一種思想力量,而不同的思想家、文學家所說的風骨又隨著他本人的思想而有所差別,這是比較符合劉勰全書的原意的,也和當時各個藝術領域中所論的風骨可以協調一致,同時也能比較妥善地解釋《風骨》篇的原文。”(注:張少康:《文心雕龍新探》,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131頁。)此說從《文心雕龍》全書立論, 是有根有據的,而且認為“風骨”是劉勰追求的一種美,也很有學術眼光。只是“精神風貌”的提法似比較籠統,還可進一步斟酌。
第八種,“內容形式”說。認為“風”是內容,“骨”是形式。
第九種,“形式內容”說。認為“風”是形式,“骨”是內容。
以上兩說最缺少說服力,其論者只是從現代的文學理論的內容與形式的概念出發,不顧劉勰的原意,一味“以今套古”,不像其他說法那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本可不舉出這兩說,但為了說明目前對劉勰的《風骨》篇解釋的混亂,還是舉出,以備讀者參考。
第十種,認為要從“劉勰的理論體系的相互關系”中來看“風骨”處在理論體系中什么地位,弄清楚一系列概念的內涵和關系,從整體來把握局部,這樣才能使對“風骨”的解說接近劉勰著作的實際。這個看法當然是很好的,但由于不同的學者對《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的
看法有差異,甚至有很大的差異,結果對“風骨”的解說還是“各說各話”,難于達成一致意見。如寇效信和牟世金兩位先生,都認為應該從劉勰的理論體系切入來理解風骨,但由于二人對劉勰的理論體系看法不同,所得出的結論還不能完全一致。前者認為“‘風’是作家駿爽的志氣在文章中的表現,是文章的感染力的根源,比擬于物,猶如風;‘骨’是文章語言端直有力,骨鯁遒勁,比擬于物,猶如骨”。后者則認為“風、骨、采的關系相當于志、言、文的關系”,“‘風’是對情志的要求,‘骨’是對‘言辭’的要求,‘采’是對‘文采’的要求”(注:參見寇效信《論風骨》和牟世金《從劉勰的理論體系看風骨論》,此二文均收入《〈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下。)。
除了以上“十說”外,還有其他種種說法,恕我不再一一羅列了。
為什么對劉勰的“風骨”論的解說會出現這么多的分歧意見呢?除了人們已經指出的“風骨”是一個抽象的比喻,可以作出多種解釋外,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解說者的方法各不相同所造成的。我感到目前在解說“風骨”論上,起碼存在著以下五種方法的分歧:
第一,解說劉勰《文心雕龍·風骨》論是主要以本篇為立論的根據呢,還是主要從《風骨》篇以外的篇章尋找旁證,并以旁證代替“主證”。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例如把“骨”解說為“事義”的論者,就主要不是從本篇找到的證據,而是從《附會》篇的“事義為
骨鯁”這一句話得出的結論。應該看到,《文心雕龍》全書用到“文骨”、“骨鯁”、“風骨”、“骨髓”等詞語的共有32處之多,差不多每一處都有特殊的語境,語境不同,詞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我們不是從《風骨》篇特定的語境出發來解說“風骨”,而是主要靠別的篇章尋找旁證,這是很“危險”的。如果我們根據《附會》篇“事義為骨髓”,就把《風骨》篇的“骨”解說為“事義”的話,那么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根據《體性》篇的“辭為膚根,志實骨髓”,而把《風骨》篇的“骨”解說為“志”呢?還有,我們可不可以根據《宗經》篇的話“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而把《風骨》篇的“骨”解說為“經”呢?我們可不可以根據《誄碑》篇的“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而把《風骨》篇的“骨”解說為“訓典”呢?……如果我們只是根據旁證來立論,我們對一個特定的概念的解釋就會從一種意義滑到另一種意義,這樣我們就永遠找不到對《風骨》篇的“風”和“骨”的確定的解釋。我的看法是,旁證有時是可以用的,但一定要辯明語境,在語境相同或相似時,我們才能使用這種方法。對一個問題的解說,還是要以“主證”為主,“旁證”為輔,對《風骨》篇中的“風骨”的解說,必須以本篇所提供的根據作為解說的主要憑借。
第二,與第一點相關的另一個方法問題是,解說《風骨》篇的“風骨”概念,是僅抓住本篇
的某一句或幾句作為論說的根據,還是要統觀全篇的邏輯結構,貫通起來把握。從理論上說,當然是后一種方法更科學,但在實際解說中,有的論者抓“務盈守氣”這一句,有的論者就抓“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這一句,有的論者就抓“結言端直”和“意氣駿爽”這一句……這樣,《風骨》篇的“風骨”的含義也就同樣從一種滑向另一種。如何運用統觀《風骨》全篇的邏輯結構,作出全面的而非片面的把握,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第三,把《風骨》篇看成是提出新的概念和范疇的獨立的篇章,還是把《風骨》篇看成是《體性》篇的補充或進一步發揮,這也是一種方法的選擇。的確,《體性》篇在前,《風骨》篇緊隨其后,這里是不是有內在的關系,這是值得研究的。把“風骨”解說為一種風格的論者,就是認為《風骨》論不過是一篇風格的專論而已。但這里也有不少可疑之點,如既然劉勰把“風骨”看成是一種風格,那為什么在篇中更多的是把“風”和“骨”分開來論述呢?難道作為風格的“風骨”是由兩種東西拼湊起來的嗎?劉勰其他篇都是一篇一題,為何單單風格問題是兩篇一題呢?看來,把《風骨》篇看成是提出新的概念與范疇的獨立篇章是更合理的。
第四,是從魏晉以來流行的人物評品來研究《風骨》,把劉勰的“風骨”論看成是從人物評
品中“移植”過來的概念,還是著重尋找劉勰“風骨”論的“淵源”?這也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種選擇。有的論者主張“移植”論,認為劉勰的文學“風骨”論只是人物評品中術語的借用,因此可以通過對人物評品問題的研究,來解說劉勰“風骨”的含義。有的論者則認為劉勰的文學“風骨”論是他的獨創,與當時流行的人物評品關系不能說沒有關系,但關系并不大,倒是應該從更遠的淵源上來追索劉勰文學“風骨”論的成因,如從《毛詩序》的“詩之六義”來考察“風骨”的原始意義,并從這里展開對文學“風骨”論的解說。我個人認為兩種都有其合理性,但后者的合理性大于前者的合理性。
第五,是從劉勰的文學理論體系來探討“風骨”論,還是把《風骨》篇孤立起來研究。當然,大家都認為前者更可取,但劉勰的文學理論體系是怎樣的呢?這就又有分歧,如前所說,對劉勰的文學理論體系的掌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劉勰文學理論體系的理解不同,對“風骨”的解說會產生不同的解說。但是我認為對劉勰的文學理論體系的把握盡管困難,卻仍然是值得為之努力探求的。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對劉勰文學“風骨”論的解說的分析,歸根到底是由論者所選擇的不同的方法所造成的。方法的正確選擇才是解開劉勰的“風骨”之謎的根本。但困難的還在于,并不是在兩種方法中選擇一種,而是要在上述五種方法的分歧中,進行綜合的選擇,而且所選擇的幾種方法,能夠構成一個互相匹配的完整的系統。這也是本文希望達到的目標。
二、“風骨”是劉勰對文學作品內質美的規定
我們要了解劉勰的“風骨”是何含義,如前所說首先要從劉勰的《文心雕龍》的文學理論的整體理論體系出發。劉勰的文學理論一般認為可以分為總論、創作論、作品論、欣賞論、發展論等五論,“風骨”論屬于作品論。作品論的內容很豐富,但就作品的構成而言,劉勰認為,文學作品的構成要素不外乎兩大要素,這就是“情”與“辭”。劉勰在《文心雕龍》許多篇中都指出了這一點:
志足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征圣》)
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此立文之本源也。(《情采》)
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辭情。(《熔裁》)
若夫立文之道,唯字與義。(《指瑕》)
以上四條在論作品的構成上,語境極為相似,都是從宏觀的視角、根本的規律上來談文章的構成要素。《征圣》篇的一條是從孔子論一般人的修身要做到“情欲信,辭欲巧”,轉而談到構造文章的金科玉律是兩點:志足情信,言文辭巧。從這里也可見,劉勰認為作品的
構成分為情與辭兩個方面,是受到了孔子論人的修身的論點的啟發而提出來的。《情采》這一條最為明確,作品作為實體由經線和緯線編織而成,而經線是“情”,緯線是“辭”,這是“立文之本源”。《熔裁》一條也很重要,意思是說上百節的骨節構成人體,必須依靠血脈的貫通,萬種意念構成文章,離不了辭與情兩個要素。《指瑕》這條,也是講構成文章的根本道理,劉勰認為字與義是構成文章的兩要素,如果對文學作品而言,這里的“字”實際上是“辭”,這里的“義”實際上就是“情”。這四條可以證明劉勰確把“情”與“辭”看成是構成作品的兩大要素。在明確了這一點的前提下,劉勰才進一步對“情”與“辭”分別提出了內在的審美品格的要求。換言之,“情”與“辭”是構成作品的必要條件,只要有“情”與“辭”,不論“情”是否真切,“辭”是否“巧麗”,作品就可以成立;但是對優秀的作品來說,僅有一般的“情”與“辭”的外部“包裝”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對“情”與“辭”提出內質美的要求。《風骨》篇就擔負了論述內質美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