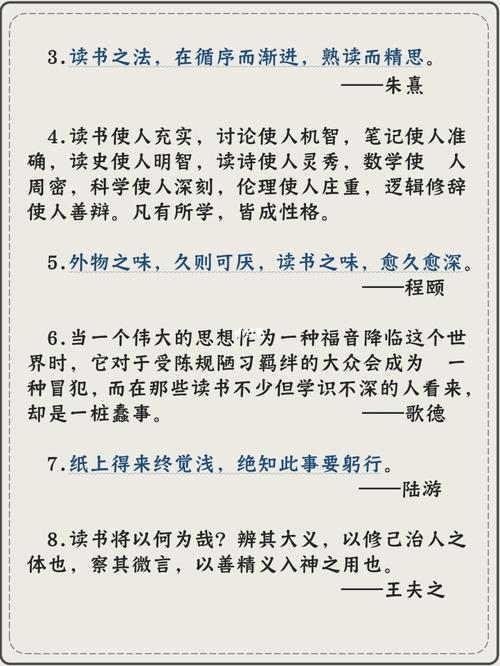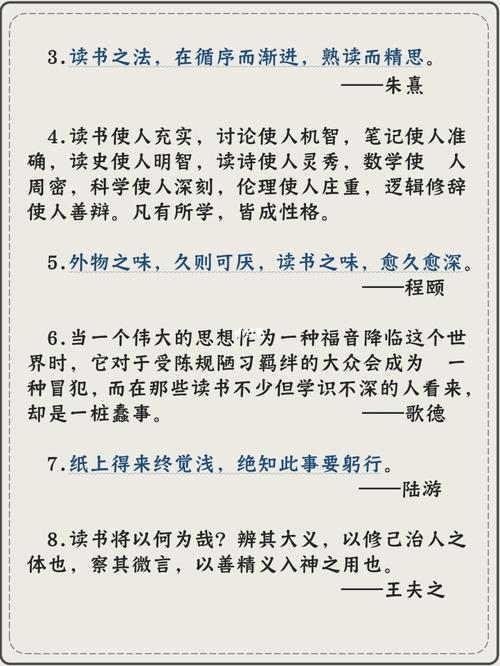
游園驚夢藝術特色.txt騙子太多,傻子明顯不夠用了。我就是在路上斬棘殺龍游江過河攀上塔頂負責吻醒你的公主。白先勇的《游園驚夢》賞析
瀏覽次數:39291次懸賞分:10|解決時間:2006-11-8 13:53|提問者:天籟風神
問題補充:
是小說
最佳答案
白先勇在小說《游園驚夢》中有意識地采用了敘事學方法及互文性思路。小說在外視角敘述中加入局部人物的內視角,并把兩種敘述視角相互結合、穿插,進而通過內視角的回顧性敘事,自然轉入意識流中的詩意表達。與此同時,中國文學的豐厚傳統給予作品互文性以極大便利,并營造了“人在戲中,戲在戲中”等多方面的藝術效果。由此,又構成了夢醒時分的寬闊的闡釋空間。
關鍵詞:《游園驚夢》;敘事視角;意識流;互文性;闡釋空間
白先勇的小說《游園驚夢》是《臺北人》系列小說中的一篇,完成于1966年。1981年改編成同名舞臺劇,在美國和臺灣演出均獲得巨大成功。忠實于小說的意蘊,又配以演員出色的表演、優美的音樂以及服飾、舞美,共同構成了一個凄美哀婉的世界和一個人或一群人夢醒時分的痛苦。小說《游園驚夢》已經成為漢語讀者非常喜愛的文學經典,本文有意識地選用一些批評方法,對《游園驚夢》進行文本分析,探尋其藝術價值形成的機制。
一、敘述角度的自如轉換與意識流手法中的詩意表達
由于中國傳統白話小說脫胎于話本而擅長于敘述,其敘述視角基本采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敘述、描寫、議論、抒情自然地融合于無所不知的敘述者。這個敘事傳統滋養了古代小說家,也為現代小說家所嫻熟。白先勇既充分地繼承傳統敘述的自如便捷,又富有創造性地拓展了敘述視角,達到了傳統手法與現代手法的圓融,突出體現于三個層次敘述的遞進。
第一個層次,《游園驚夢》在第三人稱敘述視角中加入局部人物的第一人稱視角,并且兩種敘述視角互相結合、穿插。這個特點主要體現在小說開頭和前半部分。小說開篇,敘述者面對一群軍界官員和將軍夫人們,這些人大多經由南京、上海來到臺灣,空間在時間
的隧道中變遷,其間榮辱盛衰、人世更替、生離死別,有很多撕心裂肺的故事,只有采用俯視角的第三人稱敘述,才能統觀審視和把握。人的心理世界和感情線索對于小說太重要了,白先勇深得個中三昧。因此,他不滿足于時代風云變幻的客觀記錄,他需要進入人物心理和感情深處,以便寄予對人生、愛情乃至人世的理解。如何解決既有俯視角的歷史敘述,又有感情和心理的深度描繪這個難題?在第三人稱俯視角敘述中穿插人物視角的局部敘述,成為作家的藝術選擇。
西方經典敘事學認為,第三人稱敘述同時可以具有“外視角”與“內視角”。作為“內視角”的人物的眼光往往較為主觀,帶有偏見和感情色彩,而作為“外視角”的故事外敘述者的眼光則通常較為冷靜[1](P217)。所以竇夫人桂枝香大宴賓客,邀請昔日得月臺唱昆曲的各位姐妹們,這個起筆就采用了俯視角。引出了錢夫人后,敘述視角便轉為錢夫人這個內視角:“竇公館的花園十分深闊,錢夫人打量了一下,滿園子里影影綽綽,都是些樹木花草,……錢夫人一踏上露臺,一陣桂花的濃香便侵襲過來了……”在竇夫人指引下,錢夫人一一見過諸位客人,這些客人也都是從錢夫人眼光看到和接觸到的。這個視角非同一般,錢夫人經歷過榮華富貴,見識過各種公館,竇公館自然地被置于比較視野中。至于這些客人,有南京時的舊相識,比如天辣椒蔣碧月,賴夫人、劉副官等,也有在臺北興起來的新
人,比如徐經理徐太太,程參謀等,新人與舊人同時處于一個場合,從經歷了歷史變故的錢夫人眼光看出去,引發的感慨當然具有特殊的意義。
第二個層次,錢夫人出場后,雖然沒有“我”這樣的標志性第一人稱敘述者出現,但是因為頻繁地采用錢夫人視角,實際上已經采用故事中人物的眼光來敘事了。于是,敘述視角發生了一個重要變化,即出現了敘事學所指出的第一人稱回顧性敘事。在這種回顧性敘事中”通常有兩種眼光在交替作用:一為敘述者‘我’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為被追憶的‘我’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1](P238)。如果我們將從錢夫人眼光看到和感覺到的認作是第一人稱回顧性敘述,就會發現,錢夫人確實在追憶,現場的人、景物和氛圍都是勾起她回憶的條件。但錢夫人如今所知肯定會比當年在南京時所知的要多,她在追憶,也在重新回到當時的體驗。比如,客人們都到齊了,竇夫人來請大家入席,人們推讓著,竇夫人讓錢夫人先坐下。這時“錢夫人趕忙含糊地推辭了兩句,坐了下去,一陣心跳,……倒不是她沒經過這種場面,好久沒有應酬,竟有點不慣了。從前錢鵬志在的時候,筵席之間,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錢鵬志的夫人當然上座,她從來也不必退讓……可憐桂枝香那時出面請客都沒份兒,連生日酒還是她替桂枝香做的呢。到了臺灣,桂枝香才敢這么出頭擺場面,……”這樣的追憶連帶著也傳達出了當年的體驗,這個視角具有比較和引起傷感的功能…
…
第三個層次,意識流敘述線索。錢夫人的人物視角敘事,仿佛在積蓄力量,當酒力上來,錢夫人的感情也蘊積到相當程度時,意識流呼之欲出:完全中斷竇公館宴請賓客唱昆曲的現實線索,在錢夫人意識流動中回到當年在南京酒席清唱會的情境中去。《游園驚夢》的圓熟精致的藝術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后半部分采用意識流手法且轉換自然。白先勇自己曾經說過:“我寫這篇小說寫了五次。前三次用比較傳統的手法寫內心的活動,我都不滿意。起初我并沒想到要用意識流手法。女主角回憶過去時的情緒非常強烈,也有音樂、戲劇的背景,為了表達得更好,嘗試用了意識流手法。”[2](P267)自然地轉換為意識流手法,這符合人物心理規律。英國心理學家瓦倫汀(Walentine)、貝爾納(Berlyne)、海爾森(Helson)等,都提出過漸進喚起理論。他們的實驗審美心理學認為,人們的審美情趣,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慢慢地調動起來的,無論是從作家創作角度講,還是從讀者接受角度講,都有一個心理喚起過程,即由簡單到復雜,由直白進入曲折,由緩慢發展到緊張的漸進過程。其實,這也是人的一般心理規律。在竇公館豪華鋪排的宴席上錢夫人多喝了幾杯花雕,又受到天辣椒的刺激,眼前景象喚起了當年在南京清唱會的景象,天辣椒如何對待她的親姐姐桂枝香,勾起了在南京清唱聚會上發現自己親妹妹與自己情人鄭彥青鄭參謀的
私情,一陣急怒,啞了嗓子。此刻,由于聽到《游園驚夢》,觸景生情,心理上又重新經歷了一次她一生中最痛苦的經驗……以往經驗和眼前情境所形成的合力喚起并且推動了錢夫人的意識流動。意識流“這是威廉&S226;詹姆斯在他的著作《心理學原理》(1890)里所使用的一個詞組,特指在一個清醒的頭腦中,源源不斷地流動著的思想和意識。‘意識流’現在表示現代小說的一種敘述方法……自20年代始,意識流就成了文學敘述的一種模式。作家利用它來捕捉人物的心理活動過程的范圍和軌跡。在這一過程里,人的感覺認知與意識的和半意識的思想、回憶、期望、感情和瑣碎的聯想都融合在一起”[3](P34》)。在這個文本中,錢夫人意識流獲得了豐厚的藝術效應。第一,原本是竇夫人宴請的場面與故事,現在變成了眼前的竇公館故事和當年錢夫人在南京酒筵清唱會上故事的重疊。兩個時間橫斷面上的兩個故事,在錢夫人意識流中重疊在一起。讀者閱讀過程不斷地辨析兩個故事,實質是給自己講故事。他們理解了兩個故事的關系,也就理解兩個故事重疊的深層含義。第二,借助于意識流手法捕捉到了昆曲的旋律。文本中意識流動中仿佛起到靈魂一樣作用的是音樂,這不僅表現在不斷地出現《山坡羊》《皂羅袍》等各種曲牌名字和《牡丹亭》里的唱詞,而且表現在意識的流動完全隨著音樂旋律而前行,讀者捕捉到了音樂旋律,也就對于錢夫人意識中的豐富復雜的內容有了理解,而理解錢夫人意識中的豐富內涵,也就欣
賞了昆曲藝術。第三,錢夫人的意識流將情緒引向高潮,在文本中自然地形成了跌宕起伏的效應,一個圓熟、和諧并且具有波瀾之美的藝術品就這樣臻于完成了。
重要的不是作家采用了意識流手法,而是如何采用意識流手法。以上三個層次交錯和遞進,可以看做是作家將意識流置于其他敘述手法的和諧使用中。又因為其中的情緒和感情似乎都被中國傳統文化所浸透了,所以,在我看來,《游園驚夢》成功地采用意識流手法,得益于將意識流的內容放在中國傳統文化豐富內涵的平臺上,與中國傳統文學、文化互相交融,這就涉及到這個文本的”互文性”問題了。
二、中國文學的豐厚傳統造就了優秀的“互文性”小說藝術
采用“互文性”方法分析《游園驚夢》,是探尋這個文本藝術價值的另一條路徑。“朱力亞&S226;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為指涉(intertextuality)這一術語,表示任何一部文學文本‘應和’(echo)其它的文本,或不可避免地與其它文本互相關聯的種種方法。這些方法可以是公開的或隱蔽的引證和引喻;較晚的文本對較早的文本特征的同化;對文學代碼和慣例的一種共同積累的參與等”[3](P373)。克里斯蒂娃關于“互文性”的思想啟發了我們:誠然,“互文性”超越于國家和民族,各民族國家的文學互相借鑒、互相指涉的空間是無限的,但不可否
認的是,對于民族國家文學來說,其歷史越悠久,貯存越豐厚,文學創作中“互文性”的空間就越大,“互文性”也隨之越加突顯,讓我們帶著這個啟示分析《游園驚夢》的互文性與中國傳統文學。
小說中互文現象頻頻出現。題目是借用了《牡丹亭》五十五出戲之一的《驚夢》及劇中游后花園的情節,其實也是直接借鑒昆曲《游園驚夢》的題名;小說描寫的酒宴、唱昆曲的情節和傳統劇目《貴妃醉酒》有情節的相似之處;錢夫人和錢將軍的婚姻,以及情節中穿插的錢夫人、程參謀、天辣椒蔣碧月等談論表現曹子建和宓妃愛情的戲曲《洛神》,與隨從參謀的戀情等情節,都與曹植《洛神賦》描述的濃郁愛情意蘊有相似之處,有弦外意味;引用的一些曲牌名,比如《夜深沉》《將軍令》《萬年歡》《點絳唇》等也都與情節、人物的感嘆有多向的微妙聯系,都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形成引喻。我所描述的互文現象分別來自這個文本“已經形成的形象或者意象及其隱喻”“文學作品的客觀世界。這是存在于象征和象征系統中的詩的特殊‘世界’”以及”‘形而上性質’(崇高的、悲劇性的、可怕的、神圣的)”[4]等這些層面。我的問題是,如果說,互文現象分布在作品各個層面,彌散于文本的藝術整體中,那么,在作品構成與藝術價值形成中起到了怎樣的作用呢?
1.人物關系與“互文性”。人物觀和功能觀是傳統小說觀和結構主義小說觀的根本區別之一。比如,主張人物觀的福斯特(E.M.Forster)在《小說面面觀》中基本在故事層討論小說,他關注的主要問題是:故事、情節、人物、幻想、預言、布局和節奏等,對小說敘述規律探討很少[5]。確實,傳統文學批評在人物關系的理解上,基本落腳于情節結構方面,認為人物是中心,也是推動情節發展的動因。功能觀則強調人物在整個文本結構中可能起到的作用,這啟發了我們,能否在人物關系中發現其他藝術功能呢?比如在互文中發現其他功能?錢夫人是小說中最主要人物,她與宴會主人竇夫人以及竇夫人的親妹妹天辣椒蔣碧月,構成了一個有共同在南京得月臺唱昆曲的過去,也有再聚首的今天;她們不是一般的相識,是地位此起彼伏的舊雨新知;特別是在嫁人這個重要人生轉折點,她們形成人生糾葛。她們的相互關系是在時間隧道中逐步紐結而成的。在故事的現在進行時,又頻頻以姊妹相稱,這種鼎足三立的人物關系,自然形成“三姊妹”的外觀印象。考據白先勇是否有意識地借鑒俄國作家契訶夫的多幕劇《三姊妹》的人物關系及意蘊,不是本文的任務,我關注的是互文的效果。哥倫比亞大學夏志清教授、柏克萊加州大學白之教授(CyrilBirch)看了《游園驚夢》舞臺劇的錄像,都曾經拿契訶夫的《三姊妹》來比[2](P271)。《三姊妹》的戲劇情節從有意義的一天里開始:父親逝世一周年暨伊利娜命名日,在這一天,姊妹三人
與父親昔日的部下圖贊巴赫中尉、維爾希寧中校相遇、相識,并且發生了感情糾葛,為她們后來的人生埋下了伏筆。劇情悲涼并且驚心動魄,劇終,奧麗迦擁抱著兩個妹妹,寬慰并且鼓舞著妹妹:“啊!我的上帝啊!時間會消逝的,我們會一去不返的,我們也會被后世遺忘的,……然而,我們現在的苦痛,一定會化為后代人們的愉快的;幸福與和平,會在大地上普遍建立起來的。后代的人們,會懷著感謝的心情來追念我們的,……多么愉快呀!叫人覺得仿佛再稍稍等一會,我們就會懂得我們為什么活著,我們為什么痛苦似的……我們真恨不得能夠懂得呀!啊!我們真恨不得能夠懂得呀!”[《》(P337)在人物構成和悲涼命運等方面,契訶夫的《三姊妹》與白先勇的《游園驚夢》極為相似,“三姊妹”似乎可以成為覆蓋這類人物關系及人生意味的意象,只不過《游園驚夢》中的三姊妹故事時間與空間的變遷讓意蘊更復雜而已。《游園驚夢》對于《三姊妹》的關聯方式是極為隱蔽的,或者說是借助于《三姊妹》已經在讀者心目中產生的意義而強化和播散《游園驚夢》自身的意義。由此,我們發現人物結構不僅推動情節發展,而且已經成為模式,并且在互文關系中產生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