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19日發(作者:迅雷b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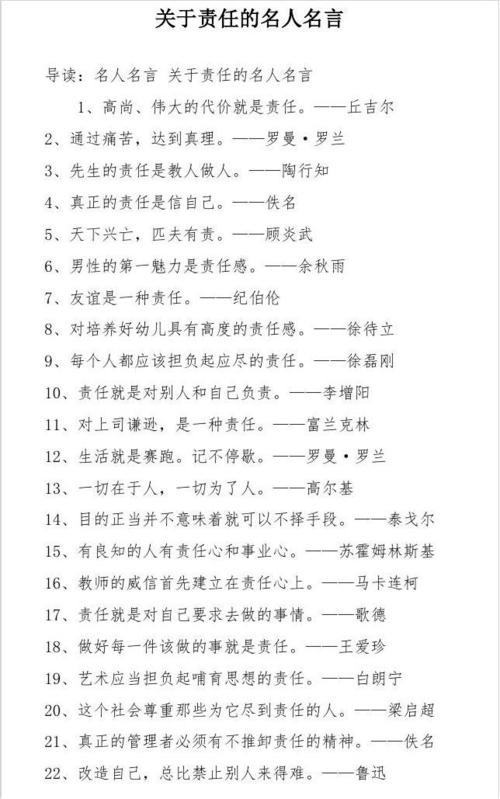
孫德喜:尷尬沙汀
著名作家王蒙曾經描述了自己在1980年代的一度尷尬:“我好像是一個界碑,這個界碑還有點發胖,多占了一點地方,站在左邊的覺得我太右,站在右邊的覺得我太左,站在后邊的覺得我太超前,站在前沿的覺得我太滯后。前后左右全都占了,前后左右都覺得王蒙通吃通贏或通‘通’,或統統不完全入榫,統統不完全合鉚合扣合轍,統統都可能遇險、可能找麻煩。”(王蒙:《王蒙自傳·大塊文章(第二部)》,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156頁)類似王蒙的這種尷尬,其實30多年前在沙汀身上就發生過。1950年初,沙汀一夜之間“從舊政權的階下囚一變為新政府的主人”(吳福輝:《沙汀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55頁)論理來說,沙汀應該興奮和激動才是,應該表現出躊躇滿志。但是,他卻陷入了尷尬:“解放區的文化人看他是國統區的進步作家,國統區的朋友視他為根據地出身的黨內干部。”(吳福輝:《沙汀傳》,第355頁)雖然無論是國統區還是解放區的文化人士都沒有將他當作敵人,但是雙方面都沒有將他當作親近的朋友,他可以從中感受到自己處境的微妙窘迫。身于這樣的處境,內心涌起一股悲涼是可想而知的。
解放區的文化人將沙汀視為國統區的作家,是有根據的,也是意味深長的,而且沙汀與巴金、胡風等國統區作家不同,
他的最大問題是從解放區,——而且是革命圣地延安——去了國統區的,這就不能不讓人產生無盡的猜想。盡管沙汀自己可能覺得問心無愧,對革命一直保持忠誠,但是別人未必認同。沙汀的出身雖然比較復雜,但是他一旦投身革命,便義無返顧。1904年,沙汀出生于四川安縣一個在當地頗有地位的家庭。他家住在安昌鎮西街,祖上留下了可觀的田產。他所誕生的楊家大宅,可以與巴金小說《家》中的高公館相比,同樣掛著“國泰家慶”與“人壽年豐”的對聯。雖然沙汀的父親在五六歲的時候就已去世,他的母親獨立支撐起這個家庭,但是這個家庭并沒有立即垮掉,更何況沙汀的舅舅鄭慕周是當地勢力強大的袍哥會的頭面人物,因而,沙汀在青少年時期沒有像魯迅喪父后那樣受人歧視,遭到冷遇,而且能夠受到良好的教育。盡管沙汀當時的生活條件還不錯,但是在讀書時不僅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且對政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25年,原名楊朝熙的沙汀閱讀了發表共產黨人理論文章的《中國青年》,深受影響,竟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楊只青”,取的意思是“只有青年才有前途”(吳福輝:《沙汀傳》,第65頁)。與此同時,沙汀對辨證唯物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思想開始向革命方面傾斜。1927年初夏,沙汀在革命遭受嚴重挫折的情況下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事革命工作。1929年,沙汀來到了上海與周揚、周立波等人組織和領導左翼文藝運動,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沙汀投入了小說創作,
從而成為革命者兼作家。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沙汀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中去,一方面參與集體創作“大眾體長篇小說”(吳福輝:《沙汀傳》,第176頁)《盧溝橋演義》,一方面到前線去慰問抗戰官兵、采訪傷兵。忙碌了一陣之后,許多文化人感到上海生存越來越困難,于是決定離開上海,疏散到大后方,繼續從事自己的事業。于是,沙汀回到了他的家鄉四川。回到家鄉,沙汀安頓好妻兒以后,迅速與這里的文化人取得聯系,全力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并創作小說。如果沙汀就這樣在四川一直待下去,他雖然不一定會改變將來的命運,但是或許可以減少對他的某些不信任和猜疑。但是就在1938年,沙汀受到當地青年學生奔赴延安的激蕩,于是向組織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很快得到了組織的批準。經過18天的艱難行程,到了延安,沙汀見到了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鼓勵和支持,于是立即要求到前線去采訪。但是,由于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正缺人,再加上老朋友周揚的挽留,沙汀只好暫時放棄了到前線的計劃。在魯迅藝術學院工作不久,遇到了賀龍將軍到這里發表演講,他對賀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不僅從賀龍身上感受到的威嚴,而且發現賀龍特別詼諧,充滿著農民的智慧。沙汀于是決定要通過采訪,為賀龍寫點東西。很快賀龍離開延安到前線去,而且向“魯藝”要人充實部隊各級干部,恰巧“魯藝”的一期學員學習期滿,沙汀便抓住這個機會,隨學員一起跟賀龍到前線去。沙汀去
的時候“多少帶點浪漫成分的心愿”(吳福輝:《沙汀傳》,第215頁),但是,跟著部隊生活了一段時間,那種“浪漫”便漸漸消退了,代之而來的是嚴重的煩惱和焦慮。在隨部隊的行軍過程中,沙汀與和他一道來到部隊基層何其芳覺得自己簡直成了部隊“喂養的兩匹牲口”(吳福輝:《沙汀傳》,第222頁),原因是他們在與部隊的行軍中,“只是雜亂無章地跟著吃、睡、走路,不了解敵我情況,不能訪問,不能工作,變成了部隊的負擔”(吳福輝:《沙汀傳》,第222頁)。這讓他們這些文人覺得自己是個“局外人”,而且“軟弱而無用”(吳福輝:《沙汀傳》,第227頁),于是產生了嚴重的自卑心理。而且,他們與士兵之間悄悄地產生了裂隙和隔膜。在部隊里,“營以上的干部才有馬騎,而為了這群知識分子就需專門配備一支馬隊。當馬伕的戰士,往往與他們的關系很僵,認為他們是特殊階級。”(吳福輝:《沙汀傳》,第227頁)顯然,無論是沙汀還是士兵在那種環境里,都有對能打仗的崇拜而忽視了不同身份的人之間的差異,沒有看到知識分子的某種不可替代的功能。盡管沙汀等人并不懼怕作戰部隊的艱苦條件,而且做好了與官兵們同甘共苦的心理準備,但是由于缺乏軍事知識,對具體環境不熟悉,再加上體能上不如官兵,更容易讓官兵們對他們產生誤解和誤會。不僅如此,沙汀在行軍中先后三次丟了行李,令他最心痛的是,他在過平漢路的夜里將非常珍貴的筆記丟了。沙汀苦悶,何其芳同樣感到
苦悶,他在苦悶時“回憶他早期的詩作”(吳福輝:《沙汀傳》,第227頁)。沙汀則以“喝上一臺酒,吼幾句京戲,或者干脆讀其芳的手抄詩稿”(吳福輝:《沙汀傳》,第227頁)宣泄苦悶。他們身在自己的軍隊中,與自己的在一起,卻感到十分孤獨和落寞,其尷尬可想而知。與此同時,沙汀看到根據地的農民與他家鄉的農民沒有什么區別,都有“保守、自私、狡猾、貪圖實利種種弱點”(吳福輝:《沙汀傳》,第231頁)。如果說四川的農民是國統區的農民,擁有那些缺點是可以批判的,那么解放區的農民則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應該具有很高的覺悟,但是實際上卻一樣,究竟如何描寫和表現這里的農民?看來沙汀心里是很困惑。此外,沙汀在文藝思想上,“與延安的某些主流理論不合”(吳福輝:《沙汀傳》,第235頁)當時延安的主流文藝理論強調幾千年的文化遺產的精華和民間創作的重要,而沙汀與何其芳卻反駁,他們認為“僅僅強調大眾藝術,會‘降低藝術水準’”(吳福輝:《沙汀傳》,第236頁)。結果,缺乏政治頭腦的他們被人扣上“將藝術脫離抗戰,脫離政治”和“新的藝術至上主義”的大帽子。沙汀心里不服,雖然可以與人家吵上一通,但是被扣上的帽子不是輕而易舉可以甩掉的,心里肯定擺脫不了這個陰影,要想爽快起來不那么容易。于是,在寫完賀龍的書之后不久,他正式提出了返回四川的請求。對于這次返回故鄉的原因,長期以來沙汀沒有解釋,“他不能理直氣壯地講出回故鄉創作
的動機,那很容易誤解為不愿寫解放區/也不能給自己安上‘臨陣脫逃’的罪名”(吳福輝:《沙汀傳》,第358頁),倒是賀龍在50年代初的一次春節會議上為他打了圓場,說他由延安回四川是“老公跟起老婆走”(吳福輝:《沙汀傳》,第357頁)。
如果是從國統區來到延安,那自然是受到充分的肯定,而且在革命隊伍中寫起自傳來一定非常自豪,也一定會大書特書;如果是組織上要求到國統區工作,那么也會得到“服從革命需要”或者“聽從領導安排”等肯定性的評語。而沙汀則不同,他是自己向組織上請求的。盡管組織上也同意了,但是在延安那些們看來,多少總有些問題,在情感上也可能有些微妙之處。不知沙汀后來是否感覺到這點,他當時終究還是離開了。如果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沙汀當時離開延安還是非常明智的,不知他當時是否已經預感到某種不祥之兆,就在他離開延安以后,那里發起了整風運動和搶救失足者運動。如果沙汀還待在延安,以他復雜的社會關系和人生經歷很可能遭遇不測,在嚴厲的政治審查中被扣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關進監獄,遭受迫害都有可能。即使沒有遇到嚴格的干部審查,但是在整風運動中,同王實味、丁玲、艾青、蕭軍一樣受到敲打敲打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的“四川脾氣”(吳福輝:《沙汀傳》,第236頁)決定了他在整風運動中不會交上好運。
沙汀于1939年11月與妻子玉頎離開延安,并沒有立即回到了他的老家川西北的安縣,而是先到了重慶,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了一段時間。1941年“皖南事變”標志著國共兩黨自抗戰以來合作關系的破裂,共產黨人在重慶的處境非常艱難而危險,中共南方局決定疏散在重慶的共產黨員作家,疏散地主要是延安和香港。在延安的周揚托人帶信給沙汀,希望他重回延安,“重慶組織上似乎也有這個暗示”(吳福輝:《沙汀傳》,第267頁)。沙汀此時在心中也作了權衡,最終決定還是回老家安縣。沙汀心里很清楚,他的老家決不是理想的去處,那里是國民黨和袍哥會的地盤,各種社會矛盾錯綜復雜,而他這個共產黨人回到那里,無疑是十分危險的,而且也是困難重重的,形勢對他來說肯定是非常嚴峻;回延安去,固然是回到了們中間,但是過去在延安的經歷他一定記憶猶新,歷歷在目,回到那里心情未必舒暢。更何況他的創作長于批判和諷刺,在延安很難有用武之地(新中國成立以后,他的批判和諷刺同樣沒有用武之地),而家鄉的人和事,山和水,草與木,他是那樣的熟悉,家鄉許多人的音容笑貌都刻在他的腦海里,成為他取之不竭的創作源泉。經過這一番權衡,沙汀最終決定疏散到自己家鄉。
果然,他在家鄉沒有得到安逸和溫馨。他的共產黨員身份迫使他過著半流亡的生活,按照吳福輝的說法,“他注定要為此付出代價和得到代價”(吳福輝:《沙汀傳》,第269頁)。當
他回到他曾經生活過的安縣城關安昌鎮西街的楊家老宅時,沙汀已經找不到當年的“安謐、寬敞”(吳福輝:《沙汀傳》,第270頁)和舒適的家的感覺了。他本來指望就在這里繼續寫作他的長篇小說《淘金記》,但是這里現在“破敗得像一床爛棉絮,連空氣都是陰沉、死滅,無法忍受的。”(吳福輝:《沙汀傳》,第271頁)沙汀只好另覓住處,并且不得不與妻、兒分居。雖然沙汀有舅父鄭慕周的庇護,但是政治迫害還是“尾隨而來”。1942年春夏之交,安縣來了個神秘軍官楊穗,在他的訛詐下,鄭慕周不得不讓沙汀離城躲藏。這樣,沙汀只好一個人躲到離城十里的鄉下。鄉下的條件雖說不錯,但是沙汀卻失去了自由,相當于被軟禁起來,搞得他“一點寫作的欲念也提不起來”(吳福輝:《沙汀傳》,第277頁)。不久,這個令人討厭的楊穗走了,沙汀以為自己的政治避難結束了,自己可以自由活動了,但是很快他就聽到了成都行轅密令縣府逮捕自己的消息。鄭慕周為了安全起見,只好將沙汀安排到非常偏遠的地方去避難。這次他來到了距安縣城60多里遠的睢水。主人同樣出于安全考慮,將沙汀安頓在一個三層樓上,他“整天關在這個房間里,絕對地不出街一步。”(吳福輝:《沙汀傳》,第280頁)過了一段時間,沙汀才與外界取得了聯系,并且“在停筆半年之后,終于決定要用筆把這個禁錮他的世界,戳個窟窿,使自己能夠稍稍透出一口氣來。”(吳福輝:《沙汀傳》,第281頁)然而,他也僅僅是
通過與外界的聯系“稍稍透出一口氣來”而已,他的生活仍然處于地下狀態,他還不能公開活動,不能走出庇護他的場所。他所能做的只是悄悄地寫作,至多可以獨自從后門出去到河灘邊散步。隨著時間的推移,沙汀感覺到威脅在漸漸的淡薄,便大著膽子到街上走走,甚至到茶館里坐坐,隨后他還可以將岳母與妻子接到身邊來,從而使他的孤獨得到了緩解。直到1942年秋寫完小說《淘金記》,沙汀在睢水才過上正常人的生活,融入了當地人的社會生活中。可是僅僅略微松了口氣,沙汀在中秋節前夕又得到了要逮捕他的消息,不得不趕緊收拾點文具和簡單的生活用具,到睢水以南更加偏僻的苦竹庵去避難。1943年初,國民黨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政治形勢逆轉,沙汀的處境更加嚴峻,他在舅父的安排下轉到了劉家溝。這里不僅更加荒涼偏遠,而且條件更是簡陋,主人劉榮山給他臨時騰出的屋子,“塞滿酸菜罐子,發散出一股令人作嘔的臭氣。破爛家具偏沒有一張桌子,最要命的是沒有窗戶,也就是沒有白天寫作所必需的陽光。……有一面墻是上段是用破曬席夾成的。”(吳福輝:《沙汀傳》,第301頁)沙汀在這里上午伏在木柜上艱難地寫作,下午獨自一人出門爬山,散散心,同時活動活動筋骨。他在這樣的條件下創作了長篇小說《困獸記》的大部分篇幅。1944年春,沙汀在散步時遇到一片罌粟,便疑心有人要以此為借口前來抓捕自己,于是神經緊張起來,在一個深夜里匆匆逃離。一場
虛驚之后,沙汀又回到了苦竹庵,專心繼續寫完《困獸記》。直到1944年初夏,沙汀在何其芳的幫助下才離開這里重返他闊別3年多的城市,當他從大山里鉆出來時,“朋友們幾乎認不得他了。”(吳福輝:《沙汀傳》,第305頁)一到重慶,沙汀就參加了文藝界的整風學習,重點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學習,沙汀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盡管他在深山里創作的《淘金記》受到了一些朋友的贊揚,但是拿自己的創作與毛澤東的這個講話一對照,他發現了問題,他的作品所描寫的基本上都是“農村小市民以上的人物”,與毛澤東所倡導的刻畫工農兵形象相距甚遠。“如果按照整風文件衡量,似乎不是主要的寫作方向。”(吳福輝:《沙汀傳》,第307頁)這樣一對照,沙汀難免不感到忐忑不安,內心同時產生了羞愧。此時,周揚再次邀請他到延安去,然而沙汀再次像上次那樣作了權衡,這次他還是以“家里的拖累”(吳福輝:《沙汀傳》,第309頁)為由謝絕了周揚的盛情與好意,實際上,他的問題在于“反映落后的生活,諷刺、暴露,是不如歌頌黨和黨所領導的斗爭來得重要,但自己只能‘退而求其次’”。(吳福輝:《沙汀傳》,第309頁)因而他在重慶待到了1942年底。由于形勢的緊張,沙汀等人又一次被要求疏散,他只得再次回到了苦竹庵。這次他在這里專心創作了《還鄉記》。抗戰勝利以后,沙汀的處境不僅沒有得到改觀,反而更加危險,國民黨四川當局對他下了通緝令,“三年,一
個長長的夢魘。在夢里總有人在背后追趕。”(吳福輝:《沙汀傳》,第336頁)“他跑到哪里,哪里都有一對兇惡的眼睛。”(吳福輝:《沙汀傳》,第337頁)住在苦竹庵,沙汀已經感到不那么安全了,“一有風吹草動,他就從睢水家出門溜上河坎,或者經紅石灘、鄧家碾房繞個大圈子,進入山岰,到蕭家避些日子。”(吳福輝:《沙汀傳》,第342頁)在苦竹庵的日子里,沙汀不僅經受著恐懼的煎熬,還要經受著孤獨、貧困與疾病的折磨。俄國作家契訶夫將沙皇統治下的俄羅斯稱為巨大的精神病院——“第六病室”,沙汀則將他在苦竹庵視為他的“第六病室”,這里的生活讓他的精神接近崩潰。與此同時,“沉重的家庭負擔加重了他的精神困境。”(吳福輝:《沙汀傳》,第338頁)由于子女多,他不得不給朋友們寫信,催促出書寄版稅。到了1948年,沙汀受到了“日漸嚴重”(吳福輝:《沙汀傳》,第341頁)的胃病的困擾,導致他的寫作幾乎停頓下來,甚至體驗到了死亡。疾病折磨了兩三個月,沙汀終于脫離了險境,身體逐步康復過來。但是,身體還沒完全康復,沙汀又不得不長途跋涉,到永興避禍。就在前往永興的途中,沙汀一到河清的一位熟人家“一頭坐下就不能動彈了”,(吳福輝:《沙汀傳》,第345頁)隨后人家雇了滑竿才將他送到永興。就這樣,直到1950年春,隨著當地國民黨政權的垮臺與解放軍的到來,沙汀才終于走出了他的“第六病室”,恢復了自由。
當沙汀走出了他的“第六病室”時,他感到了空氣的清新和呼吸的舒暢,他覺得從此“不用化裝,可以拋頭露面,不怕見任何人”(吳福輝:《沙汀傳》,第354頁)了,“解放”的感覺油然而生。然而,沙汀還沒將仔細品味這種“解放”的感覺,他就被人兜頭潑了一盆冷水。就在他坐車前往成都就任軍管會文藝處領導職務之時,與他同車的王維舟“突然”說:“共產黨員可不能操袍哥啊!”(吳福輝:《沙汀傳》,第355頁)“為了隱蔽,在哥老當中混混是可以的,現在要注意影響啦!”(吳福輝:《沙汀傳》,第356頁)這簡直是對沙汀的嚴重警告,也就是說,沙汀雖然還是自己人,但是還是需要警告一下的。如果他不是在家鄉待了這么多年,而是待在延安,現在跟著大部隊回來,那情形肯定不一樣。然而,就是在家鄉的這些年,沙汀雖然吃了不少苦頭,但是在創作上還是取得可觀成就的,他不僅創作了長篇小說《淘金記》、《困獸記》和《還鄉記》,而且還留下了數量可觀的短篇小說,而那些長期待在延安的作家生活條件與寫作條件雖然比沙汀強多了,但是其成果卻無法與他相比,從宏闊的文學史來看,延安的作家中沒有幾人的作品能夠與沙汀的相比。就是沙汀本人如果不是回到家鄉,而是一直待在延安,也只能寫寫“賀龍傳”或者《太陽照在桑干河上》之類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一時可能受到贊揚,但是隨著政治斗爭的展開也可能為其付出沉重的代價或者受到嚴厲批判。那么,他在延安與家鄉之間選
擇了后者究竟該如何看待?相信沙汀即使經歷的1950-1980年代的各種政治波瀾他都不會后悔的。
到了成都,沙汀雖然坐到了領導的位置上,但是他得補上延安的那一課,學習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黨的文藝政策,與大家一道“洗腦筋”(吳福輝:《沙汀傳》,第356頁)。他雖然懂得“文藝為政治服務”,對集體主義與紀律性有明確的認識,但是真正按照這些理論和要求去做,還得有一個適應的過程。他得通過思想改造清除頭腦中一切不符合政治要求的東西,特別是被指為“自由散漫”的思想和習慣。盡管如此,他還是遇到了令他不解的現實:他的朋友林如稷將他的《我所見之賀龍將軍》印出來,而且相信一定會暢銷,但是卻碰了壁。林如稷“忘掉了新社會的書籍事業已經由國家統一管理。川西的宣傳部門對解放之初用一本書來宣傳賀龍是否合適,改變做不得主,提出要請示上級。書被扣住不得發行。”(吳福輝:《沙汀傳》,第358頁)想當年,在國民黨統治下,作為共產黨員的沙汀雖然在地下狀態寫了許多小說和散文,但是還能夠在國統區出版發行,而今到了自己人執政,就連歌頌共產黨將軍的作品都被扣,不能發行。真不知沙汀想到這事,他的心里到底是啥滋味!不僅如此,沙汀的尷尬愈益顯得突出,組織上在他的檔案材料中寫下了這樣的話:“因該長期不過組織生活,應加強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學習。”(吳福輝:《沙汀傳》,第359頁)更令
沙汀感到尷尬的是當年保護過他的人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而遭到了鎮壓,有的人在遭槍決前游街時據說還念著沙汀的名字罵。沙汀聽到這些消息后“心里的感受是挺復雜的。”(吳福輝:《沙汀傳》,第359頁)當年人家保護了自己,現在人家有難,沙汀卻無能為力,沒有給予絲毫保護,沙汀能不感到愧疚嗎?其實,沙汀也很無奈,且不說當時他可能不知道那些保護過他的人遭到了鎮壓,就是知道了他也沒有辦法,幫不了忙,因為他在組織那里沒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他如果出面替那些幫助過他的人講話,就可能被認為喪失階級立場,政治覺悟有問題,進而受到批評。
或許是沙汀長期在國統區生活,沒有經過延安的政治的淬煉的緣故吧,沙汀在就任文藝界領導職務之后,對于文藝的某些看法和主張也與某些領導不一樣。比如,擔任重慶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兼文聯黨組書記的邵子南“主張首先加強思想改造,然后才能寫作。”(吳福輝:《沙汀傳》,第363頁)而沙汀和艾蕪則認為:“讓大家寫,寫出來不好,批評它就是‘改造’。”(吳福輝:《沙汀傳》,第363頁)他們雖然在本質上沒有區別,但是在細微的地方有些差異,更由于他們之間的地位差距決定了沙汀與艾蕪有些尷尬。好在邵子南與沙汀的關系還算可以,所以沙汀還能夠“婉轉提出希望邵重視黨外一些資身文化人”(吳福輝:《沙汀傳》,第363頁)。只是他們之間的裂隙并沒有消除。不僅如此,沙汀與其他領導之間
的關系也是如此。沙汀參與修改的話劇《四十年的愿望》,雖然受到了文化部的重視,并且得到了洪深的指導,但是由于“具備沒有正面反映部隊對修筑成逾鐵路的貢獻”(吳福輝:《沙汀傳》,第364頁),結果令賀龍強烈不滿,大發脾氣。在沙汀這里,他已經努力按照當時的文藝主旋律去做,但是仍然不合高級官員的口味。如果說當年的沙汀雖然在軟禁和半禁錮之下進行寫作,其獨立和尊嚴還是存在的,他寫什么,怎么寫,沒有人干預,他也沒有因此而提心吊膽;如今不同了,他沒有過去的那種自由,只是他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而是認為“現實斗爭是偉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跟不上。”(吳福輝:《沙汀傳》,第364頁)為了跟上形勢,沙汀于1951年爭取到參加土改的機會,第二年又參加了另一期土改,希望搜集新的創作素材,準備寫一部反映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但是當他進入創作時,他陷入了郁悶和痛苦之中。他“對寫新農民沒有把握”,“不能把農民寫得比工人完美,也不能‘泄氣’,這太難了。他想起去年10月紀念魯迅誕生七十周年時寫過的文章,用檢討的姿態談過去的創作‘暴露過多、光明太少’的毛病。可面對剛剛‘解放’的農民,發現自己的思想調整遠沒有完成。他不知道光明的顏料應如何調制,如何涂抹。他的筆提起來,卻在一個絕好的題目面前凝住了。”(吳福輝:《沙汀傳》,第370頁)當然,在不是沙汀個人遇到的問題,而是許多來自國統區的作家面臨的共同困境,而這個困境看似
文藝創作中的歌頌光明與暴露黑暗的問題,實質上是創作自由喪失的問題,他們在創作之前就得按照別人的思想觀念構思,而不是根據現實生活去思考,這樣的狀況怎么不陷入尷尬呢?沙汀此時“最深的痛苦是失去了‘自己’的思想,不能寫‘自由’最想寫的。”(吳福輝:《沙汀傳》,第382頁)作為一個作家,不能停止寫作,而沙汀偏偏是那種視創作如生命的人,與那些將寫作視為通向官位的跳板的人完全不同,然而沙汀的創作卻不符合極權體制下的文藝要求。問題是沙汀與當時許許多多作家一樣,沒有看到這樣的矛盾,為了爭得創作的權利,只能向體制靠攏,努力按照極權政治的要求去看待問題。大躍進當中,沙汀在雙龍、尊勝看到了無休止地該土、并社、夜戰帶來的弊病,看到大躍進中農村工作中的盲目蠻干,不講科學性,“但是經過‘反右’,只要有一絲的懷疑從腦際掠過,他也會用學來的‘主流’論、‘本質’論,一一加以澄清。群眾積極性挫傷產生的不滿,用‘階級斗爭’學說一套,也便釋然。”(吳福輝:《沙汀傳》,第395頁)他在故鄉看到最真實的現實,然而經過“思想”的過濾,結果因“不夠‘典型’”而被全部篩掉了。于是,他“先驗地在尋找與‘政策’對應的例證。他沒想到‘先進’的試點是按照特殊的條件形成的,可能是最真實的虛假。他遠遠看不到‘全部’。‘生命力的奔馳’駛入錯誤的航道,釀成的是悲劇。”(吳福輝:《沙汀傳》,第395頁)他的朋友艾蕪也是如此。艾蕪到北京十三陵水庫去,寫
了幾十萬字的半成品長篇小說,造成的不只是精力的浪費,而是他后來的創作“擱淺了”(吳福輝:《沙汀傳》,第396頁)。此后,沙汀聊可欣慰的參加了對長篇小說《紅巖》的修改,小說在全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可惜的是“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為此付出的心血”(吳福輝:《沙汀傳》,第399頁)。在隨即到來的1962年,沙汀竟然“沒有寫成任何一篇新作品。他交了白卷。”(吳福輝:《沙汀傳》,第407頁)一個作家整整一年都寫不出東西,這是多么羞愧和尷尬的事!雖然還有其他作家也可能“交了白卷”,但是對于一個視創作為生命的人那是多么痛苦啊!如果深入探討沙汀的寫作中斷的原因,恐怕還源于一波又一波的文藝大批判,一部又一部作品被貼上“封、資、修”的標簽而被打入冷宮或者受到批判,沙汀雖然沒有受到批判,但是他的內心也一定噤若寒蟬。當“接連傳來的什么什么是修正主義作品,三十年代文藝要重新估價,五六十個作家要受到批判等消息”傳來時,沙汀“變得不知所措”,“他終于什么也寫不出來。”(吳福輝:《沙汀傳》,第422頁)這意味著沙汀的文學生命進入了休克狀態。到了“文革”前夕,沙汀發現“過去肯定的、贊揚的、采取的,今天卻要否定、批判、放棄。”(吳福輝:《沙汀傳》,第425頁)身處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沙汀“除了強迫性的自我反省,檢查自己身上的‘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文藝黑線流毒’,還能做什么?”(吳福輝:《沙汀傳》,第425-426頁)他沒有發現,他此時所處
的現實已經背叛了他當初參加革命的理想,背叛了他為之奮斗的事業。而這是絕大部分革命者所忽視的,因而他們只能困惑、迷惘和壓抑,只能扭曲自己去適應這背叛了歷史的現實,并且承認自己有“罪”。而現實的嚴酷對他們的扭曲適應并不滿意,還要對他們發動更凌厲的攻勢。隨后到來的“文化大革命”,既革了文化的命,也革了他們這些投入到革命中來的人的命,將他們拉上批斗大會,對他們進行肆意的侮辱和痛打,甚至將他們投進了監獄。1968年,沙汀以“三十年代的黑干將,全省文藝黑線的大頭目,‘三家村’成員”等罪名被關進臨時監獄昭覺寺。1940年代,沙汀在國統區雖到處避難,居無定所,大多處于半幽禁狀態,但是他畢竟沒有被投入監獄;而今他被抄了家,被囚禁,沒有人給他提供庇護。時光流轉,世事變遷,真是不可思議!歷史竟是這樣的不可理喻。
“文革”的災難摧殘著人,但也促成人的思考。走出監獄的沙汀面對著嚴酷的現實,開動了腦筋,“他想不通‘整’周恩來的人為什么會受到毛澤東的信賴?而任何疑慮落到毛澤東的身上便無形消解了。這個崇高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復存在,那么中國一代的共產黨人是無法想象該怎樣思考、怎樣行動的。”(吳福輝:《沙汀傳》,第440頁)盡管沙汀“想不通”,但是他畢竟思考了,巴金當年也是同樣的“想不通”,但是一旦遇到成熟的條件,他就會將這些“想不通”的問題搞清楚了,
他的散文《思路》真實地記錄了他思考清楚的問題。至于沙汀后來是否想通了這些問題,吳福輝在《沙汀傳》中沒有交代,但是據我猜測,如果他讀到他的好友巴金的《思路》,也一定會拍手贊成,他也可能由此而弄清楚他人生尷尬的根本原因。 孫德喜,《獨立作家》專欄作家。1960年出生于江蘇淮安的農村,在鄉下生活了20年。大專畢業后,在中教系統工作8年,主要擔任語文教師。碩士畢業以后在蘇北某高校任教。世紀之交在武漢大學讀博士,2003年回揚州大學文學院工作,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這些年來,教過幾門課、出了幾本書,發表過幾篇文章、參加過幾次學術會議、跑過幾個國家、交了幾個朋友,喝過幾杯濁酒,寫下幾首歪詩。座右銘為“在自由中逼近真理,在有限中開拓無限。”獨立作家投稿信箱:tanys1980@ 自由寫作精神,無所顧忌。來稿請注明“獨立作家” 字樣。

本文發布于:2024-02-19 14:42:25,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本文鏈接:http://www.newhan.cn/zhishi/a/1708324945269292.html
版權聲明:本站內容均來自互聯網,僅供演示用,請勿用于商業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在24小時內刪除。
本文word下載地址:孫德喜:尷尬沙汀.doc
本文 PDF 下載地址:孫德喜:尷尬沙汀.pdf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