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0日發(作者:總結)

窯洞,學府
一堵崖面,三只窯洞,就是學校所有建筑;一個老師,二十幾個學生,就是全體師生員工;一片廢鐵懸掛于老師辦公室(邊窯一)前的木樁上,一根鐵勺柄被一根細麻繩吊在木樁的另一側,“當當當”上課,“當當”下課,“當當當當當……”集合,老師就用這個最簡陋的設備發號施令,它也就成了學校的象征;教室(主窯)有上下相疊而開的小窗、中窗、大窗,一則為了采光,二則是為了顯示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力度——普通農戶乃甕牖繩樞之家,是沒有能力在一孔窯洞開這么大的三口窗且用木頭做窗框,用玻璃擋西北風的。土坯上支幾頁木板,就是桌子,麥草袋子壓在屁股下就不能叫草包,該改口叫凳子,至于那一面被人字木架支起的用墨錠染得黑一道白一道,或者說黑里泛白木板,當然就是黑板了。另一孔窯洞是師生灶,它和農戶的灶房幾乎一樣,只不過陳設更為簡陋,一擔木桶,一口水缸,一個小案板,直徑不到一尺的黑鍋,一只碗,一雙筷子,如果你是被別人蒙了眼送到這間灶房,你肯定會根據這些家當判定是到了一家光棍的廚房里,子孫滿堂是和這間屋子聯系不起來的,更不敢想象它就是師生灶。這就是我記憶中的村學,是我學習點橫豎撇捺,認識加減乘除的小學,它簡陋得如同掩映在雜草叢中的鄉村戲臺,鑼鼓不響,演員不登場,是沒有人會想到它的存在的。可我把它不叫學校,更不叫窯洞,而把它叫做“學府”。冠以如此美譽,不是因為它有多少尖端科研項目,而是因為它傳承的氣息,早已融入了我的血脈,我的呼吸不止,它的味道不減。
太陽比較古板,按時東升西落,不會因為孩子們需要看書,多在天空停留一兩個時辰,點燈又沒有油,明亮的電燈泡還亮在收音機的新聞里,我們只能從大人們“亮得地上掉一根針,晚上都能看得見”的言談中揣摩電的神圣。這就省去了早晚自習,在家里我們也不用趴在燈下抄寫,正好幫家里做些零活。老師經常教導我們要熱愛勞動,熱愛勞動人民,勞動可以創造財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人,勞動人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勞動最幸福,勞動最光榮……如果說黃土高原是流水反復沖出了溝壑,那老師在我們的小腦袋里反反復復地刻出了“勞動”二字。早晨我們迎著朝陽高唱“愛學習,愛勞動,長大要為人民立功勞”,下午我們用“小喜鵲,造新房,小蜜蜂,采蜜糖,幸福的生活從哪里來?要靠勞動來創造。青青的葉兒紅紅的花,小蝴蝶,貪玩耍,不愛勞動不學習,我們大家不學它。要學喜鵲蓋新房,要學蜜蜂采蜜糖,勞動的快樂說不盡,勞動的創造最光榮。”送走天邊的云彩。每學期通家書上,總有一句“督促學生參加力所能及的勞動”提醒家長,操行評語欄里少不了在校勞動中的表現,我們都交換著看對方的通家書上是否填了“熱愛勞動”四個字,少了那四個字,如果不哭個眼圈發紅,也得耷拉著個腦袋好幾天,像偷了人家的東西。不要以為那時候的學校勞動不過是打掃衛生而已,愛勞動與否都是老師憑印象打分,其實那時我們到三四里遠的溝里抬水是每天必上的勞動課,學校有勤工儉學基地,十幾畝平地,抬水澆樹、種菜,拔草,耘土,割蕎麥,扳苞谷,挖洋芋,打柴……這些勞作都很容易稱量出你對勞動的態度。在家里偷懶,大人們總用“小心我告訴你老師”或者“再指使不動我就在通家書上寫?假期勞動不積極?”來嚇唬我們,這是最后一招,也是最管用的一招。我們的童年,是文化大革命剛結束的時候,要說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的成績,首先就要大書特書“勞動競賽”,“勞動競賽”的種子在父輩的心田里開花,結果后,又不失時機的播撒在了我們心窩里,我們這一代人之所以能夠吃苦耐勞,那時的勞動教育,功不可沒。
光線不足造成的最大障礙在冬季。雞叫頭遍,就得摸著起床,最遲到雞叫三遍就得摸著趕十多里山路,坑坑洼洼,一顛一顛地往前揣摩,加之黑乎乎鬼影一般的山巒、樹木和貓頭鷹、狐貍的凄慘的叫聲,早使我們小小的心臟咚咚的跳,一個村里的孩子要一塊走,大孩子要領著小孩子,這是生活的逼迫,也是老師的教導,更是班里的紀律,哪一路的小孩子因為害怕不能按時到校,這一路的大哥大姐首先要挨批。關愛他人,扶弱濟困成了老師考察學生品行的第一項內容。到教室里還是黑乎乎的,看書寫字是不行的,我們就放開喉嚨唱歌,唱
《咱們工人有力量》《解放區的天》《我愛北京天安門》《學習雷鋒好榜樣》《繡金匾》《烏蘇里船歌》《南泥灣》……雖然跑調,但把積極向上愛國愛民的激情唱了出來,現在時過境遷,給我們講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我們很容易接受,因為那時就已經設置好了頻道,現在一有同步信號,就會馬上產生共振。唱困了,就輪流講故事,講《小白菜》《豆皮豆瓤》《狐貍精精》《白蛇傳》《天仙配》《三結義》《下河東》……爺爺奶奶講給的故事都可以拿出來露一手,小人書看到的情節都可以在同學面前炫耀一番。老師和同學除了仔細聽講外,笑聲和掌聲是少不了的,敘述能力和表達能力就潛生暗長在這朦朧的黎明中。故事講完了,就得背課文,背不下去,有人領著背誦,背熟了就搶著到黑板前單獨背誦,老師打分,同學評議,由于反復強化,背誦過的篇目至今記憶猶新,前天兒子翻出我的舊課本,看見課文的題目旁邊老師用蘸筆寫了六七個“背”字,愕然,追問何故,我說一篇課文老師最少要分期盯背六遍,兒子不信,我當場就把三十多年前背過的吳伯蕭的《記一輛紡車》背了一遍,兩千六百多字的文字像聽到了口令似的,依次登場,兒子驚得目瞪口呆,我又把那十幾處精彩的比喻分析了一番,說是那個時候在黑乎乎的窯洞里聽老師講,后來又把它們反復抄在作業本上才記牢的,小家伙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溫故知新,及時鞏固,分期回顧,學以致用……我的老師沒有系統的學過教育學,但他的教育思路卻科學合理,就像“老子”時代沒有懂黑格爾,但辯證法早已滲透在《道德經》中一樣,我的老師已經在學術和師德上達到了令人景仰的高度,這是目前到處抄襲論文,每周上一兩節課就叫喊加工資的所謂教授們難以企及的。
光線不足帶來的頑疾是黑板沒有合適的擺放位置,如果將它立在窯掌,學生背對著窗子,看不清書本上的字,黑板也因為離窗口過遠,上面的字還是看不清楚;如果把黑板放在窗口,學生書本上的字看清了,可黑板背光,老師的書寫,只能靠學生根據講解和粉筆運動的軌跡揣測,錯別字就難免了;擺到側面,兩邊的同學只能看到黑板有一寸寬的厚度,感覺不到黑板有多大。黑板就像一個沒有型號的螺帽,在哪一輛機器上都找不到相應的螺紋。辦法總是有的,我的老師根據光線的明暗移動黑板:早晨和傍晚,光線較暗,他就將學生分為兩組,黑板放在教室的中間,面向門口,聽講的學生面向黑板的正面,做練習、默寫課文的學生,坐在里面,面向黑板的背面;中午光線強,黑板可以放在窗子附近,雖然背光,學生還是看得清楚,三個年級可同時學的圖畫和簡譜都能在黑板上展示。老師也相應的把練習課、復習課,安排到兩頭,新授課安排到中午。有些課確實需要在早晨上,我的老師就將要講的例題或者生字、生詞寫在兩面小黑板上,掛在教室的側壁,照顧兩頭的同學,中間支一面大黑板,學生都面向側壁聽講。老師給我們常講的一句話是:“這些題我是這樣認真地做了三遍,才不出錯;那些生字、生詞我也是這樣一筆一畫地寫了至少三遍才這么俊美,你們要像老師這么認真才能學到真本領。”我們都以老師為榜樣,生字生詞反復地寫,力爭比老師寫得好;一道數學題做三遍,三遍都不出錯才算通過。現在想來,那大小不同的三面黑板,挪前挪后的一面黑板,老師像教本一樣提出提進的小黑板早已在我們的視網膜上涂上了踏實認真,一絲不茍的身影,那身影就像天安門上的國旗,早已成了一種崇高和偉大。現在我指導學生例題做三遍不出錯,可以看下一種類型題;鋼琴彈三遍不出錯,可以再加一個拍子;英語的典型例句要聽懂、背熟、寫對,作為學習其他同類型句子的模板進行比對;回答主觀題先聽老師講一遍,自己口述一遍,再動筆寫到卷子上,才能保證卷面整潔,條理清楚……這都是窯洞小學教給我的思路,是四年大學里沒有學到卻十分見效的教法。
雖然說窯洞冬暖夏涼,夏涼倒不假,冬天不生火,還是受不了西伯利亞寒流的折磨,特別是我們這些一條棉褲穿幾個冬天,褲腿時常露肉的孩子,更是沒有實力和寒流對抗,腳上、手上的凍瘡和蒼蠅換班,夏天蒼蠅上班,凍瘡休息,冬天蒼蠅剛下線,凍瘡就找我們來了,一來就是一個冬天不回家,有時還磨蹭半個春天。教室里用土坯壘起一個土堡,土堡里唯一的鐵制構造就是爐條,爐筒子是買不起的。燃料就是細煤和土倒成的煤塊,可這煤塊也不夠用,多是山里撿來的干柴,一旦生火,教室里濃煙滾滾,嗆人的氣味使全體師生集體咳嗽,
只能將窗子打開。寒風將窯里的濃煙趕凈,也將爐火帶來的溫暖一并驅逐出門。“生火”不能“取暖”,要上課,就得挨凍。搓手、哈氣、跺腳,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影響老師的講課。對付寒流,沒有上策,但也有下策:老師在門外抹了一個土堡,生了一團伙,我們凍得實在受不了了,就到火爐旁烤一烤,烤熱了進來上課,但這樣秩序太亂,出出進進,分散學生的注意力。老師把困難匯報到生產隊長那里,生產隊派勞力,給三孔窯洞的后面排了三個土炕,每個土炕可以坐十多個學生,一個年級正好一個土炕。師娘將炕燒得滾燙,整個窯里都熱氣騰騰,混合著微微的煙草味,給人一種家的溫馨。我們借著微弱的亮光,在小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寫著“我們愛老師,老師愛我們……”,老師給一年級講解完,布置任務后又到另一孔窯洞上二年級的課,二年級的課還沒講完,三年級的學習委員又在門口報告,說它們已經做完了習題,等老師好半天了。我們都趴在熱乎乎的炕上,老師卻在三孔窯洞里穿梭,像發動起了的拖拉機,不關油門,就一直往下跑。師娘的飯煮熟了,誘人的香味使我們老咽唾沫,再也聽不進去“段落大意了”,師娘讓我們吃一口,“不吃”;師娘讓我們吃一個,“不吃”;師娘讓我們吃兩個,“……”我們經受不住師娘的反復強化,小黑手終于接過了冒著熱氣的粗面饅頭、玉米棒子、洋芋疙瘩、蕎面攪團……爸爸媽媽知道后,先是罵我們“丟人”,后來又督促我們帶些吃食,給老師填補饃籃,那年月,誰的日子都不好過。盡管師娘多次推讓,可最后還是收下了。老師覺得長期這樣不好,就讓我們把凍成鉛球的饅頭收集起來,讓師娘托熱,那個不到一尺大的黑鍋,師娘得耗一早上的功夫為我們盡義務,我們一副饞狼般的吃相,老師和師娘顛一臉笑佛模樣瞅我們狼吞虎咽。門外寒風呼呼,門內卻春風拂面。前天來了個測字算命的,讓我在他手心寫兩個字,我先寫了“老師”,他說你是老師就不要寫這兩個字了;我又換成“師娘”,他說和老師有聯系,再換兩個字;我換成了“窯洞”“土炕”“大學”。他說這一下沒聯系了,我說還是有聯系,這是我人生的“關鍵詞”《大學》有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善。”意思是說,大學的宗旨,是在于弘揚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棄舊迎新,使人的道德達到最完善的境界。按這個標準衡量我的母校,叫它“大學”,你看恰當否?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我們那時蒙受了老師“涌泉之恩”,但我們沒有“江海之蓄”只能用“滴水”相報。老師備課,批改作業,我們給他翻本子;老師改卷子,我們加分,登記成績;老師的衣服臟了,有高年級女生捶洗;老師柴垛矮了,我們使它長高長胖;老師的面缸見底了,我們哭著鬧著向爸媽討,討不來了,就到麥地里撿麥穗,豆角地里拾黃豆,洋芋地里刨尋遺漏的“白蛋”“紅蛋”;上樹掏鳥窩,下夾子逮野兔,用小鐵鏟挖山芋,下雨后采蘑菇,拾地軟軟……把老師的的灶房變成雜糧店。現在有報道說日本的孩子有很強的野外生存能力,我說他們是夜郎自大,如果敢和我們一比高下,就像他們自以為是的圍棋手遇上了聶衛平,非敗不可。這得益于老師訓練我們自救的秘方——凡是學生從山里淘回來的,老師一并“笑納”,還要表揚,享用的時候還要分給大家,還要加幾句“將來能干大事”的鼓勵。如果是偷來的,或者是討來的,堅決不要,還要點名批評,更要雙手捧送給主人且道歉。我們這些窯洞學校里畢業的學生堅信“有一雙手是不會被餓死的”。我們從這所“大學”一畢業,馬上就有了“工作”。
如今,和我一同讀村學的二十多個同學中,有上了“西北師大”的,有“人民大學”讀了研究生的,還有“北京大學”讀了博士的,可我們一說起母校,首先想到的是窯洞里的書聲,和那些足以稱作教育家的老師,至于那些別人羨慕的高校反倒居其次了。
本文由《文章馬伊琍網》/ 負責整理首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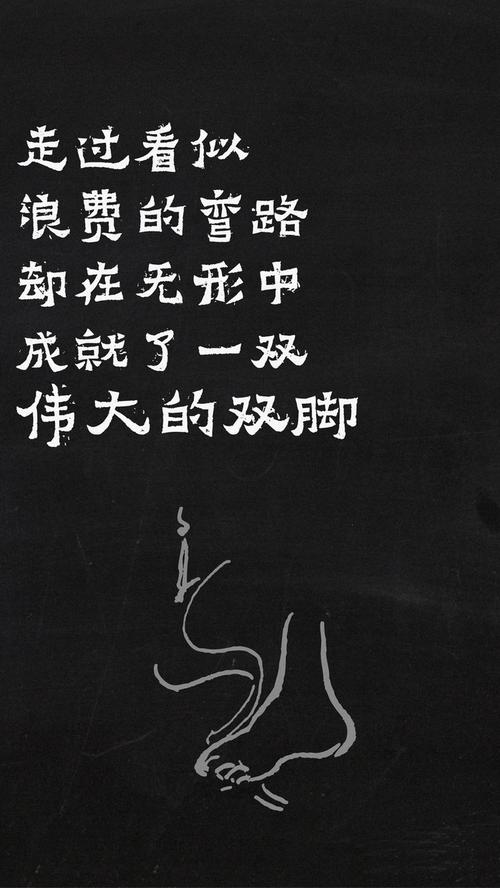
本文發布于:2024-02-20 05:52:54,感謝您對本站的認可!
本文鏈接:http://www.newhan.cn/zhishi/a/1708379575145095.html
版權聲明:本站內容均來自互聯網,僅供演示用,請勿用于商業和其他非法用途。如果侵犯了您的權益請與我們聯系,我們將在24小時內刪除。
本文word下載地址:窯洞,學府.doc
本文 PDF 下載地址:窯洞,學府.pdf
| 留言與評論(共有 0 條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