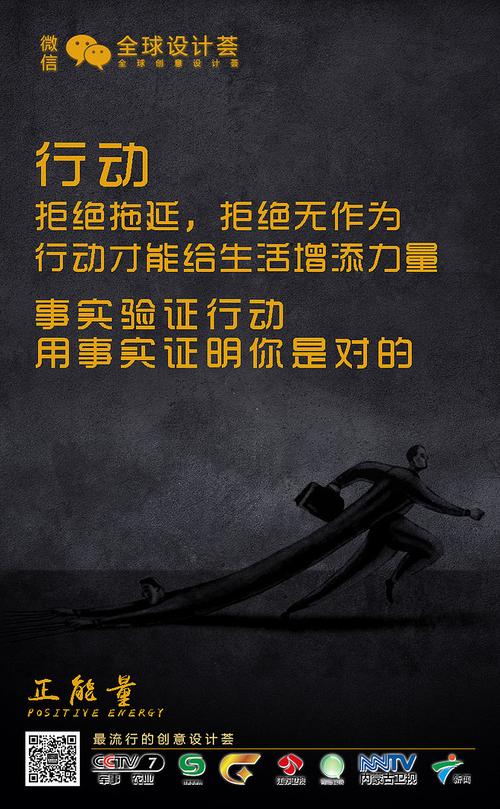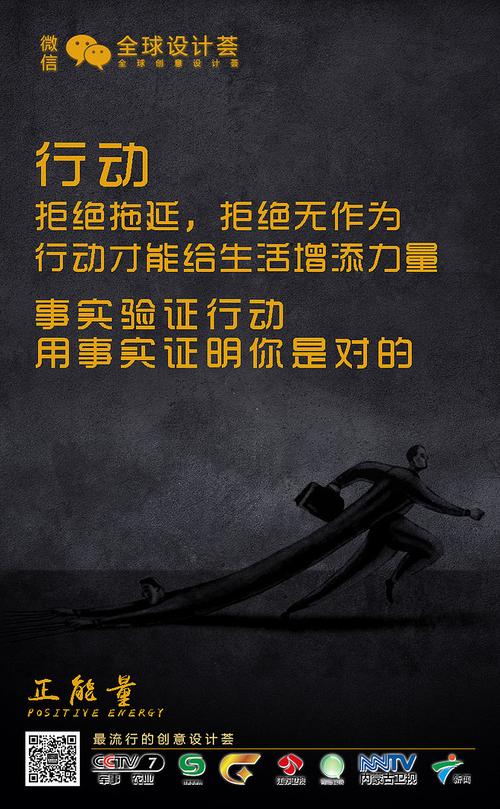
民俗學(xué)抑或人類學(xué)?──中國(guó)大陸民間信仰研究的學(xué)術(shù)取向
*導(dǎo)讀:一、前言在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研究中,概念或范疇是學(xué)術(shù)討論的重要基礎(chǔ)。民間信仰作為一個(gè)被反復(fù)構(gòu)建的范疇,……
*一、前言
在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研究中,概念或范疇是學(xué)術(shù)討論的重要基礎(chǔ)。民間信仰作為一個(gè)被反復(fù)構(gòu)建的范疇,并非是一個(gè)靜止性的概念,內(nèi)涵與外延充滿著不確定性,因而也富有開(kāi)放性。英文世界中的Folk Religion、Folk Belief、Popular Cult、Popular Religion、Communal Religion ,都可能指涉所謂的民間信仰。該術(shù)語(yǔ)最早見(jiàn)于1892年的西方學(xué)術(shù)期刊,1897年日本學(xué)者姊崎正治亦正式用之。約在1920年代民間的信仰、民眾信仰、民間宗教常見(jiàn)于中國(guó)學(xué)者的文章中。至1930年代民間信仰已成為一個(gè)相對(duì)穩(wěn)定的術(shù)語(yǔ)了。[1]
在中國(guó)大陸或臺(tái)灣地區(qū),約定俗成的民間信仰范疇,通常指具有宗教性又有民俗性雙重維度的信仰形態(tài),用以指稱那些與建制性的宗教形態(tài)(如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宗教、新興宗教或教派)相區(qū)別開(kāi)來(lái)的混合性的信仰形態(tài)。從發(fā)生學(xué)的視角看,民間信仰一方面?zhèn)鞒辛烁髅褡寤蜃迦旱淖匀恍宰诮蹋ㄗ詾樯桑┑膫鹘y(tǒng),另一方面也傳承了建制性宗教(有為
建構(gòu))的傳統(tǒng),帶有村社(村落和社區(qū))混合宗教的典型特征,堪稱原生性和創(chuàng)生性雙性共存的復(fù)雜的信仰形態(tài)。當(dāng)然,它的信仰對(duì)象不僅僅只是屬于庶民的,更是屬于精英的,甚至可以是傳統(tǒng)國(guó)家宗教祭典的一部分(正祀)。民間信仰盡管未具有觀念或儀式體系的內(nèi)在一致性,諸如信奉某至上神,經(jīng)由先知啟示,排他性的教典教義等等,但顯然都具有超自然性的特征,特別是從未脫離神靈化(如神、鬼、祖先)、巫術(shù)化(黑白巫術(shù))、數(shù)術(shù)化(計(jì)算性、操作性)等三重向度。
自從上世紀(jì)中國(guó)引進(jìn)并創(chuàng)建了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體系之后,中國(guó)民間信仰研究便成為多個(gè)學(xué)科的關(guān)注對(duì)象。當(dāng)然,中國(guó)大陸真正有學(xué)術(shù)意義的民間信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1978年以來(lái)的30年。因此,本概述將集中評(píng)述該時(shí)段中國(guó)大陸的學(xué)術(shù)成果,并探討民俗學(xué)與人類學(xué)研究取向的得失。必須聲明的是,近年來(lái)民俗學(xué)和人類學(xué)的科際整合和學(xué)科交融成為一種趨勢(shì),故而這種學(xué)術(shù)取向的界定只是為了清晰敘述的方便,而非欲給研究者劃分陣營(yíng)或標(biāo)簽。[2]
*二、民俗學(xué)研究取向
中國(guó)民間信仰的民俗學(xué)研究取向,系發(fā)端于上世紀(jì)20-30年代。在學(xué)科意識(shí)尚未精細(xì)化或細(xì)碎化的年代,中國(guó)民俗學(xué)內(nèi)生的傳統(tǒng)便是兼顧文本與田野、考古與考現(xiàn)、文化與生活
的。民俗學(xué)者更是學(xué)科上的多棲者。出于到民間去、喚起民眾的文化自覺(jué),他們一開(kāi)始便將觸角伸向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彌漫的反迷信或打倒迷信的意識(shí)形態(tài)中,從而鑄就了現(xiàn)代民俗學(xué)執(zhí)著切入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品格和傳統(tǒng)。如顧頡剛在《妙峰山》中感言應(yīng)當(dāng)知道民眾的生活狀況,朝山進(jìn)香的事是民眾生活上的一件大事,決不是可用迷信二字抹殺的[3]云云;容肇祖在《迷信與傳說(shuō)》中強(qiáng)調(diào)研究民俗學(xué)離不開(kāi)中國(guó)的迷信,拼命高呼打倒某種迷信的時(shí)候,往往自己卻背上了一種其他的迷信[4];江紹原在《中國(guó)禮俗迷信》中堅(jiān)稱,應(yīng)該詳加考察迷信這個(gè)概名的來(lái)源和歷史、意義與內(nèi)容[5]。當(dāng)然,諸如楊得志所譯的Charlotte Burne《民俗學(xué)問(wèn)題格》昭示著民間信仰問(wèn)題原本就內(nèi)生于學(xué)科意識(shí)當(dāng)中。因此,民俗性或民間性(迷信)而非宗教性成為大家的先入之見(jiàn)。蓋緣于宗教與迷信同屬于西洋的泊來(lái)品,中國(guó)現(xiàn)代民俗學(xué)最初并無(wú)民間信仰即宗教的文化自覺(jué)。
盡管說(shuō)信仰民俗或俗信研究是現(xiàn)代民俗學(xué)的學(xué)統(tǒng)之一,改革開(kāi)放前中國(guó)大陸學(xué)界畢竟無(wú)法避免政治和意識(shí)形態(tài)的窠臼,故而期間的成果略而不論。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民間信仰研究的民俗學(xué)取向并未脫離三種研究或?qū)懽鞣妒健?/span>
*其一,通論性研究的范式。
在研究基礎(chǔ)薄弱,左的意識(shí)形態(tài)影響依在的處境下,通論性研究必然而天然的缺乏解釋力,
但畢竟屬于基礎(chǔ)性的知識(shí)介紹工作,故理應(yīng)獲得一定的歷史定位。其中有兩種寫作模式的得失值得注意。
*1*、民俗學(xué)概論模式。
在汗牛充棟的《民俗學(xué)概論》中,信仰民俗或俗信成為重要的板塊或民俗門類,類同的敘述焦聚于民間信仰的范疇、內(nèi)涵及外延、性質(zhì)與特征、類型與功能等問(wèn)題。這些重復(fù)性的文化生產(chǎn)最大的附帶功能就在于撥亂反正、文化啟蒙、意識(shí)形態(tài)脫敏:一是民間信仰作為封建迷信、迷信、原始遺留物的緊箍咒日漸解套;二是民間信仰作為民間文化的特性獲得自明性、合法性的確認(rèn)。其中,烏丙安《中國(guó)民俗學(xué)》(遼寧大學(xué)出版社,1985)、張紫晨《中國(guó)民俗與民俗學(xué)》(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陶立潘《民俗學(xué)概論》(中央民族學(xué)院出版社,1987)、鐘敬文《民俗學(xué)概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具有典范性的意義。特別是烏丙安突出了民間信仰之民俗性而非宗教性的本位,洛陽(yáng)紙貴,幾乎成了民俗學(xué)界的通識(shí)。
近年來(lái),在區(qū)域民俗學(xué)研究蔚為大觀之際,概論式的寫作范式克隆迅速,并以村落民俗志的形式獲得新的生命力。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變成顯學(xué)的今天,他們真誠(chéng)地達(dá)成了地方民俗工作者的再啟蒙任務(wù)。諸如山東推動(dòng)的村落民俗志系列,地方教化頗豐,如王君政、王振
山編著的《安丘市王家莊鎮(zhèn)民俗志》。
*2*、民間信仰通論模式。
近30年來(lái),有關(guān)中國(guó)民間信仰概論性的研究作品,大多冠以中國(guó)、XX省區(qū)、XX民族等稱謂,帶有宏大敘事的特征,卻已然在深度、廣度方面有所突破,從而較全景式的展現(xiàn)了本土民間信仰的實(shí)態(tài)相和存在方式,諸如神靈譜系、歷史源流、作用功能、文化特征,等等。這類作品大多側(cè)重于文本研究和線性描述,間亦輔以豐富的田野資料,普遍受到進(jìn)化論思維的洗禮或西方宗教概念的影響,故而立論偏向民間信仰的民俗性層面;縱使兼談宗教性者,亦視之原始宗教的遺存物,較低等級(jí)的宗教形態(tài)云云。如烏丙安繼續(xù)秉持民間信仰與宗教的區(qū)別,金澤系以原初的宗教形態(tài)考論民間信仰。
其中,像李喬《中國(guó)行業(yè)神崇拜》(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社,1985),宗力、劉群主編《中國(guó)民間諸神》(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金澤《中國(guó)民間信仰》(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宋兆麟《巫與民間信仰》(中國(guó)華僑出版公司,1990)、姜彬主編《吳越民間信仰習(xí)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何星亮《中國(guó)自然神與自然崇拜》(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2)、王景琳和徐陶《中國(guó)民間信仰風(fēng)俗辭典》(中國(guó)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92)、烏丙安《中國(guó)民間信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徐曉望《福建民間信仰源流》(福建教育出
版社,1993)、林國(guó)平和彭文宇《福建民間信仰》(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汪毅夫《客家民間信仰》(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林國(guó)平《閩臺(tái)民間信仰源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林繼富《靈性高原西藏民間信仰源流》(華中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范熒《上海民間信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文忠祥《土族民間信仰研究》(蘭州大學(xué)博士論文,2006),都較有代表性。其實(shí),如果我們觀察再細(xì)膩一些,這一系列書名本身就是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體系的隱喻和記憶,諸如國(guó)族(中國(guó))、地域(福建、西藏)、族群(客家、土族)等等構(gòu)成公民社會(huì)的共同體想象,已然是研究者的文化表情了。有關(guān)民間信仰概論的研究系列由此誕生了現(xiàn)代學(xué)術(shù)的意義。
*其二,民俗事象研究的范式。
近年來(lái),信仰民俗事象研究一直是歷史民俗學(xué)和比較民俗學(xué)的厚愛(ài),并形成一個(gè)相對(duì)穩(wěn)定的學(xué)術(shù)群體。該研究取向的成果充分吸納了史學(xué)之重視考辨和文化重建的傳統(tǒng),當(dāng)然也不忽略尋找史料的田野功夫。這些作品通過(guò)描述和比較信仰民俗事象叢,厘清了諸多民間信仰的實(shí)態(tài)相及其相關(guān)的傳承性問(wèn)題。當(dāng)然,任何范式都不是圓滿自足的,諸如欠缺問(wèn)題史學(xué)對(duì)歷史處境的敏銳性、社會(huì)人類學(xué)對(duì)結(jié)構(gòu)的敏感性,終究是這類范式的切膚之痛。其中,一貫的直線思維(整體只是部分的相加)而非非線性思維(整體并非部分的簡(jiǎn)單相加)
的思考和寫作模式,無(wú)疑也大大限制了民俗事象研究的表現(xiàn)力度。作為中國(guó)民俗學(xué)之不可或缺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之一,民俗事象研究對(duì)于作為民俗學(xué)核心的民俗的表述力度,事實(shí)上從來(lái)便未過(guò)時(shí)過(guò)。因此,如何拓展該研究取向的路徑和方法,從而克服民俗學(xué)在回避生活,生活也在淡忘民俗學(xué)[6]的批評(píng),尚值得期待。
在民間信仰的民俗事象研究取向中,有幾個(gè)主題值得關(guān)注。
*1*、神靈崇拜類型的事象研究。
這種研究范式的作者群,涵蓋了一批活躍于民俗學(xué)、歷史學(xué)、民族學(xué)等學(xué)圈的學(xué)者,研究范圍更是涵蓋了漢族及少數(shù)民族的地區(qū)。像上海三聯(lián)書店中華本土文化叢書第二輯涉及門神、雷神、水崇拜、自然崇拜等項(xiàng);劉錫誠(chéng)、宋兆麟、馬昌儀主編《中華民俗文叢》(學(xué)苑出版社,1990)、劉錫誠(chéng)主編《中國(guó)民間信仰傳說(shuō)叢書》(花山文藝出版社,1995),幾乎囊括了中國(guó)民間典型的神靈類別及相關(guān)的傳說(shuō)故事。諸如朱天順主編《媽祖研究論文集》(鷺江出版社,1989)、劉慧《泰山宗教研究》(文物出版社,1994)、楊利慧《女媧的神話與信仰》(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7)和《女媧溯源》(北京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1999)、邢利《觀音信仰》(學(xué)苑出版社,1994)、葉春生、蔣明智《悅城龍母文化》(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巴莫阿依:《彝族祖靈信仰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4)、姜彬主編《中國(guó)民間文化》1994年民間俗神信仰專題、1995年地方神信仰專題,堪稱這類范式中水準(zhǔn)較上乘者的代表。而北京民俗博物館主持的多屆東岳論壇,也有效地推動(dòng)了華北民間神靈類型的研究。
*2*、特定信仰習(xí)俗的事象研究。
在涉及人生禮儀、歲時(shí)節(jié)慶、生產(chǎn)方式等信仰習(xí)俗方面,學(xué)者也投入頗多。有幾個(gè)系列頗具有特色:
*一是喪葬信仰習(xí)俗研究。從中國(guó)知網(wǎng)搜索,僅以喪葬為題名的論文達(dá)千篇之多,大量涉及喪葬祭祀和祖先崇拜問(wèn)題。在漢族研究方面,有數(shù)篇著作系以東南區(qū)域比較見(jiàn)長(zhǎng),也重視文獻(xiàn)與田野,以及域外的視野。如郭于華《死的困擾與生的執(zhí)著中國(guó)民間喪葬儀禮與傳統(tǒng)生死觀》(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2)對(duì)中國(guó)喪葬習(xí)俗背后的文化模式的探索、何彬《江浙漢族喪葬文化》(中央民族大學(xué)出版社,1995)對(duì)喪葬習(xí)俗的田野比較研究,陳進(jìn)國(guó)《隔岸觀火:泛臺(tái)海區(qū)域的信仰生活》(廈門大學(xué)出版社,2008)對(duì)閩臺(tái)及南洋地區(qū)獨(dú)特的祖先崇拜現(xiàn)象及買地券習(xí)俗的考現(xiàn)學(xué)研究,周星一系列文章對(duì)福建和琉球喪葬信仰習(xí)俗的文化關(guān)聯(lián)性研究[7]。
*二是節(jié)慶信仰習(xí)俗研究。在推動(dòng)傳統(tǒng)節(jié)慶納入國(guó)家法定節(jié)日的博弈中,那些歷史的和活
態(tài)的節(jié)慶信仰習(xí)俗成為眾多民俗學(xué)者關(guān)注的對(duì)象。諸如中國(guó)民俗學(xué)會(huì)組織出版的《傳統(tǒng)節(jié)日與文化空間》(學(xué)苑出版社,2007),堪稱是民俗學(xué)者強(qiáng)化自身公民性的一種集體表達(dá),從而讓節(jié)慶作為歷史記憶的承載者和傳統(tǒng)文明的見(jiàn)證。此外,蕭放《傳統(tǒng)中國(guó)民眾的時(shí)間生活》(中華書局,2002)、高丙中《端午節(jié)的源流與意義》、《作為一個(gè)過(guò)渡禮儀的兩個(gè)慶典》、《民族國(guó)家的時(shí)間管理》[8]等文,皆試圖清理傳統(tǒng)節(jié)日民俗復(fù)興中的信仰因素及其現(xiàn)代象征的意義。
*三是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的信仰民俗研究。顧希佳《東南蠶桑文化》(中國(guó)民間文藝出版社,1991)、姜彬主編《稻作文化與江南民俗》(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王榮國(guó)《海洋神靈:中國(guó)海神信仰與地方經(jīng)濟(jì)》(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王元林《國(guó)家祭祀與海上絲路遺跡:廣州南海神廟研究》(中華書局,2006)都涉及歷史中國(guó)的農(nóng)耕文化、海洋文化的神靈崇拜與地方社會(huì)的互動(dòng)關(guān)聯(lián)。
四是民間信仰的圖像、器物研究。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視野中的圖像關(guān)于圖像文獻(xiàn)研究的方法》一文曾經(jīng)對(duì)于圖像在宗教史及思想史研究中的意義做了深入的分析。近年來(lái),楊郁生《云南甲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汪潔、林國(guó)平《閩臺(tái)宮廟壁畫》(九州出版社,2003)、巴莫曲布嫫《神圖與鬼板:涼山彝族祝咒文學(xué)與宗教繪畫考察》(廣西人民
出版社,2004)、鞠熙《碑刻民俗志北京舊城寺廟碑刻民俗分析及其數(shù)據(jù)處理》(2007)[9]、葉濤《泰山石敢當(dāng)》(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都從信仰圖像或器物的視角做了一些開(kāi)拓性的討論。
*其三,民俗整體研究的范式。
我們所謂民間信仰的民俗整體研究取向,是指從活態(tài)的信仰民俗事象入手,參與觀察在特定語(yǔ)境下的信仰主體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狀態(tài)、歷史心性和文化表情。其研究特點(diǎn)是重視當(dāng)下的、日常的信仰生活,透過(guò)語(yǔ)境(context)看信仰民俗變遷,既審視信仰民俗事象活態(tài)的生成機(jī)制,也關(guān)照信仰生活的歷史、社會(huì)、文化背景。在突出民間信仰的民俗性、民間性、生活性之余,該研究取向也關(guān)注宗教性要素,諸如儀式過(guò)程、象征體系、主體靈驗(yàn)經(jīng)驗(yàn)或體驗(yàn)、社區(qū)性的祭祀組織等等。
如果說(shuō)民俗事象研究取向更關(guān)心歷史和現(xiàn)實(shí)中的信仰者說(shuō)什么(比如通過(guò)經(jīng)典或文本表達(dá)的),則民俗整體的研究路徑更加關(guān)注的是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人們?nèi)绾芜M(jìn)行信仰的實(shí)踐,也就是說(shuō),更關(guān)心人們都在做什么,因此也使得真正意義上的民俗志成為現(xiàn)實(shí)的可能,已然是一種方興未艾的新范式了。這表明了中國(guó)當(dāng)代民俗學(xué)的自我反思能力和自覺(jué)性的學(xué)術(shù)創(chuàng)新勇氣。
當(dāng)然,當(dāng)民俗學(xué)者傾其熱情和心力,注目于俗中的民的日常生活和本土信仰時(shí),同樣會(huì)面臨這樣一個(gè)挑戰(zhàn),即在努力成為異鄉(xiāng)的熟人社會(huì)的一員的過(guò)程中,作為民俗研究者與民俗參與者的身份、立場(chǎng),多少有混沌化和模糊化的道德風(fēng)險(xiǎn),甚至可能相互結(jié)成一個(gè)話語(yǔ)共謀的關(guān)系。作為一個(gè)被卷入的他者,到民間去的他或她又將如何面對(duì)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的關(guān)聯(lián)性和互滲性,以及在場(chǎng)的儀式--象征實(shí)踐對(duì)這種關(guān)聯(lián)性的潛在強(qiáng)化呢?因此,在一個(gè)個(gè)活態(tài)的民俗表演面前,局里局外,可能都會(huì)面臨頗具后現(xiàn)代意味的問(wèn)題:哇,民俗學(xué)家都到哪兒去了?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中,抑或告別田野?一個(gè)沒(méi)有了異鄉(xiāng)人在場(chǎng)的田野圖像,將如何尋找和記錄成為他者的方向感和相對(duì)感呢?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毋寧是,作為一種反思性或批評(píng)性的民俗志,如何真誠(chéng)地?cái)⑹鲞@種角色的互滲及文化再生產(chǎn)。
毋庸置疑,一批民俗學(xué)的叛徒[10]是真誠(chéng)地思考、真誠(chéng)地實(shí)踐、真誠(chéng)地轉(zhuǎn)向,深入社區(qū)、村落民間信仰活動(dòng)及組織形態(tài)調(diào)查,因?yàn)闆](méi)有村落或社區(qū)的民間信仰,也就沒(méi)有日常生活、民俗生活甚至本土文化價(jià)值觀、文化個(gè)性本身。民間信仰現(xiàn)象儼然成為了檢驗(yàn)民俗學(xué)整體研究取向得失的試金石。北京師范大學(xué)民俗學(xué)者群正是這種路徑選擇的試驗(yàn)者,我們姑且冠以民俗學(xué)的華北學(xué)派。
華北,還有民俗學(xué)者的家鄉(xiāng),因此成為和華南一樣熱鬧的田野工作場(chǎng)和想象共同體。諸如
劉鐵梁氏倡導(dǎo)在有限的民俗單位中進(jìn)行整體研究的學(xué)術(shù)自覺(jué)[11],書寫標(biāo)志性文化統(tǒng)領(lǐng)式民俗志,并組織跟蹤調(diào)查河北范莊龍牌會(huì),從而在當(dāng)代民俗的象征構(gòu)建及文化再生產(chǎn)的過(guò)程中扮演了富有標(biāo)志性的角色;其中高丙中更是詩(shī)意地描繪了當(dāng)?shù)匾约w崇拜為目的的博物館的合法化過(guò)程,宣稱這是傳統(tǒng)草根社團(tuán)邁向公民社會(huì)的歷程的標(biāo)志。在龍牌會(huì)這個(gè)當(dāng)代信仰事象的雙向構(gòu)建中,民間智慧與精英智慧珠聯(lián)璧合,精英的話語(yǔ)在靈巧地解釋并消費(fèi)著地方知識(shí);年度的大廣場(chǎng)加博物館式的公共儀式展演,成為民俗學(xué)者參與構(gòu)建地方意識(shí)的關(guān)鍵象征,中央與地方從此不再遙遠(yuǎn)。因此,到民間去不再是一個(gè)口號(hào),而是一種態(tài)度、一種信仰、一種實(shí)踐。[12]
在這個(gè)學(xué)術(shù)共同體的范式中,語(yǔ)境是中國(guó)民俗學(xué)者在華北及家鄉(xiāng)從事民間信仰整體研究的一個(gè)關(guān)鍵詞和常識(shí)。許多民俗學(xué)者從不同的方面積極深化對(duì)語(yǔ)境研究的理解和闡釋。為此,在共同體中的劉曉春以斬截的方式精僻地總結(jié)陳辭:語(yǔ)境中的民俗學(xué)開(kāi)始了![13]比如積極參與引進(jìn)這個(gè)話語(yǔ)的楊利慧因?yàn)橐庾R(shí)到從文本研究神話的局限,嘗試貫通女媧神話與女媧信仰,也就是說(shuō)想把神話的文本與語(yǔ)境結(jié)合起來(lái)研究。近年來(lái),她更關(guān)注文化語(yǔ)境、社會(huì)語(yǔ)境以及歷史語(yǔ)境等的綜合分析,即民間傳統(tǒng)在當(dāng)代社會(huì)和文化中的變遷與重建,及其與歷史和當(dāng)下的各種訴求之間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等等。[14]
因此,有關(guān)廟會(huì)、祭祀組織、口頭敘事等等民俗學(xué)的傳統(tǒng)話題,重新在語(yǔ)境中喜臨甘露。民俗學(xué)家作為另類的故事的歌手,顯示了口頭敘事的詩(shī)性魅力。民俗志書寫的對(duì)象,重心已然不在民之俗而是俗之民在語(yǔ)境中的在場(chǎng)。諸如劉曉春《一個(gè)客家村落的家族與文化──江西富東村的個(gè)案研究》(博士論文,1998)、吳效群《北京的香會(huì)組織與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1998)、《妙峰山:北京民間社會(huì)的歷史變遷》(人民出版社,2006)、巴莫曲布嫫:《鷹靈與詩(shī)魂──彝族古代經(jīng)籍詩(shī)學(xué)研究》(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0)、安德明《天人之際的非常對(duì)話甘肅天水地區(qū)的農(nóng)事禳災(zāi)研究》(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2003)、岳永逸《廟會(huì)的生產(chǎn):當(dāng)代河北趙縣梨區(qū)廟會(huì)的田野考察》(博士論文,2004)、王曉莉《碧霞元君信仰與妙峰山香客村落活動(dòng)的研究》(博士論文,2002)、尹虎彬《河北民間后土信仰與口頭敘事傳統(tǒng)》(博士論文,2004)、葉濤《泰山香社研究》(博士論文,2004)、楊樹(shù)喆《師公儀式信仰》(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已然形成了一個(gè)學(xué)術(shù)共同體關(guān)于信仰研究的系列文本。
誠(chéng)如劉曉春指出的,就具體的民俗事象來(lái)看,時(shí)間、空間、傳承人、受眾、表演情境、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文化傳統(tǒng)等不同因素共同構(gòu)成了民俗傳承的語(yǔ)境[15]。民俗學(xué)者對(duì)語(yǔ)境中的信仰民俗的關(guān)注,使得信仰民俗事象的呈現(xiàn)得以縱深化、立體化。因此,諸如高丙中、巴莫曲
布嫫、劉曉春、安德明、岳永逸等的整體的研究很難簡(jiǎn)單地用學(xué)科來(lái)規(guī)定其屬性。
當(dāng)然,由于一些研究成果的關(guān)注點(diǎn)在構(gòu)成信仰底色的語(yǔ)境、生活、整體等等之上,難免忽略了民間信仰作為信仰要素宗教性本身的整體性思考,如宇宙觀、崇拜體系、儀式與象征體系、信仰體驗(yàn)等,特別是針對(duì)本土文明體系和地方原生文化的結(jié)構(gòu)關(guān)聯(lián)更因此欠缺整體的觀照。由于較為欠缺宗教性的反思維度,以及未將民間信仰放在社區(qū)的宗教生態(tài)處境中考察,其中有些民俗志的立體深度難免不如傳統(tǒng)的民俗事象研究本身。
有意思的是,兩位家鄉(xiāng)民俗學(xué)者巴莫曲布嫫、安德明已經(jīng)充分意識(shí)到地方信仰民俗志寫作的反思性要素以及主體間性的表述本身,前者提出口頭傳統(tǒng)的田野研究模型共時(shí)的五個(gè)在場(chǎng):傳統(tǒng)的在場(chǎng)、事件的在場(chǎng)、受眾的在場(chǎng)、傳承人的在場(chǎng)和研究者的在場(chǎng);而后者在家鄉(xiāng)的民間信仰研究中切身感歷了成為他者的雙向可能性只有他者。因?yàn)槟吧瞬粌H在所謂的家鄉(xiāng)人當(dāng)中,而且在我們身上。在地方的民間信仰研究當(dāng)中,關(guān)注語(yǔ)境的民俗學(xué)家止于何處,非民俗學(xué)的叛徒止于何處,似乎遠(yuǎn)未成為問(wèn)題的關(guān)鍵。
值得關(guān)注的是,隨著國(guó)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目錄民俗部分將傳統(tǒng)節(jié)日、民俗祭典納入保護(hù)范疇,有關(guān)民間信仰與非遺的關(guān)系成為民俗學(xué)科新的話語(yǔ)場(chǎng)。從非遺視角開(kāi)展對(duì)民間信仰的研究,一方面使得信仰民俗事象與信仰民俗整體的互補(bǔ)研究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得民
間信仰的非遺性和合法性成為可能。
其中,高丙中《作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研究課題的民間信仰》(《江西社會(huì)科學(xué)》2007年第3期)具有指標(biāo)的意義。他創(chuàng)造的話題是:民間信仰的去污名化和在公共知識(shí)中的名符其實(shí),是非遺保護(hù)工作的一個(gè)核心問(wèn)題。建立公民社會(huì)和公民身份離不開(kāi)民間信仰的知識(shí)和話語(yǔ)在場(chǎng)。民間信仰因非遺性再次強(qiáng)化了作為民間文化、民俗文化的身份,成為歷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記憶的背影。從早期的迷信到民間文化,乃至方興未艾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民俗學(xué)界針對(duì)民間信仰的除魅化過(guò)程,除了到民間去的學(xué)科傳統(tǒng),顯然更離不開(kāi)域外異鄉(xiāng)人的喜好和評(píng)判。這種現(xiàn)代話語(yǔ)焦慮,讓我們對(duì)民俗學(xué)喚起民眾的初喚記憶猶新,仿佛是摩尼明尊對(duì)初人的召喚、對(duì)光明使者的召喚。
概而言之,有關(guān)民間信仰的民俗整體研究范式更多借鑒的是人類學(xué)提出問(wèn)題的路徑,代表了民俗學(xué)的人類學(xué)轉(zhuǎn)向[16],推動(dòng)了人類學(xué)式的民俗學(xué)的探索進(jìn)程。這是一個(gè)充滿挑戰(zhàn)也充滿喜悅的田野之旅、家鄉(xiāng)之旅。當(dāng)然,我們可能也得面對(duì)這樣的難題,即民俗學(xué)者針對(duì)民俗整體的小地方研究時(shí),因?yàn)樽约盒闹邢扔兄袊?guó)民俗、閩南民俗之類的知識(shí)范疇,難免就會(huì)先在地假設(shè)他者心中都有這些并在這些范疇之下閱讀關(guān)于小地方的描述,所以就難以預(yù)先評(píng)估這種地方語(yǔ)境中的民俗整體研究可能走向細(xì)碎化的風(fēng)險(xiǎn)[17]。畢竟民俗學(xué)的準(zhǔn)確
定位首先是研究民俗之學(xué),而不是研究俗民之學(xué),否則將繼續(xù)存在著學(xué)科合法化的危險(xiǎn)。
因此,有關(guān)民間信仰的民俗事象研究,諸如鳥之兩翼,同樣不可或缺,在參與構(gòu)建民俗學(xué)的學(xué)科譜系亦貢獻(xiàn)良多。舉個(gè)譬喻,如果說(shuō)有關(guān)民間信仰的通論式研究范式和民俗事象研究范式關(guān)注的是一個(gè)個(gè)獨(dú)立的蘋果、梨、香蕉的形態(tài),民俗整體研究范式則要關(guān)注整棵的蘋果樹(shù)、梨樹(shù)、香蕉樹(shù),乃至生長(zhǎng)的土壤和氣候,而宗教人類學(xué)或宗教現(xiàn)象學(xué)的研究取向,甚至還應(yīng)思考抽象的果樹(shù)、樹(shù)乃至森林自身。田野工作甚至未必是宗教人類學(xué)家當(dāng)且僅當(dāng)?shù)氖姑腿蝿?wù)。
*三、人類學(xué)研究取向
上述民俗整體研究范式的轉(zhuǎn)換足以說(shuō)明,圍繞著中國(guó)民間信仰這樣的鮮明主題,民俗學(xué)與人類學(xué)的學(xué)科邊界似乎越來(lái)越模糊了,并不存在異文化或本文化研究的天然分野,簡(jiǎn)單地從學(xué)科視角來(lái)劃分研究陣營(yíng)或研究取向,充其量只能是權(quán)宜之計(jì)。所謂本土人類學(xué)或家鄉(xiāng)民俗學(xué)多有重疊之處,異鄉(xiāng)其實(shí)是本國(guó)的異鄉(xiāng),皆脫不了如何看待地方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變遷、文化體系和生活方式本身,皆聚焦于信仰民俗事象(文本的,傳承性)和信仰民俗整體(生活的,當(dāng)下性)的描述和闡釋。
不過(guò),由于學(xué)科劃分的關(guān)系和數(shù)十年來(lái)中國(guó)養(yǎng)成的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民俗學(xué)取向和人類學(xué)取向的
研究路徑畢竟有些差異,如寫文化的差異,研究空間單位的差異,研究俗(民俗學(xué))的整體和研究人(人類學(xué))的整體的差異等等。倘若就民間信仰研究的視野而言,前者可能偏愛(ài)兼顧時(shí)間(歷時(shí)性和共時(shí)性)和空間(社區(qū)的或跨區(qū)域的),兼顧文本與田野,更熱衷于面(如長(zhǎng)時(shí)段的描述,跨區(qū)域、跨族群或社群的比較)的鋪陳,后者酷愛(ài)共時(shí)性的反思和社區(qū)性點(diǎn)的細(xì)描;就研究重點(diǎn)而言,前者的研究傳統(tǒng)更立足于信仰民俗的傳承性(唯此才能構(gòu)成俗),關(guān)注(人)民在俗之中,即外在的民俗性(信仰民俗事實(shí)是如何的)和社會(huì)性,或者說(shuō)作為歷史和活態(tài)的信仰民俗事象本身;后者則透過(guò)社區(qū)語(yǔ)境(context)的深描,更多的觀照信仰主體(人、民)自身,即俗在(人)民之中,反思內(nèi)在的宗教性(信仰生活是如何的),即作為整體的、日常的信仰生活本身。概而言之,在民間信仰研究的領(lǐng)域內(nèi),前者重在書寫民俗民之信俗(信仰民俗),后者偏于觀察俗民信俗(信仰習(xí)俗)之民。民俗志敘述的重心是信仰習(xí)俗的整體,若離開(kāi)了信俗,民俗志其實(shí)無(wú)以成為民俗志;民族志挖掘的是俗民(民)的整體,言信俗乃志在于信民。一定程度上說(shuō),民間信仰的民俗整體研究范式,亦可視為觀照民俗和俗民的人類學(xué)研究。
因此,前述帶有兩棲色彩的高丙中關(guān)于范莊的個(gè)案研究,在本質(zhì)上更是中國(guó)人類學(xué)的,即以本土社區(qū)為田野地點(diǎn),用民族志方法,關(guān)心大的問(wèn)題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緊張、國(guó)家與社會(huì)的
緊張、精英與民間的緊張,不過(guò)最后是落在緊張的超越。特別是近年來(lái)高氏主持的域外民族志寫作,以及對(duì)寫文化的文化反思,創(chuàng)造出不少帶有歐風(fēng)美雨風(fēng)格的話題,必將繼續(xù)刺激中國(guó)民間信仰研究的人類學(xué)書寫的深度。
倘若僅就寫文化的表現(xiàn)力度而言,與民俗學(xué)者經(jīng)常將民間信仰作為一個(gè)單列的主題(民俗)來(lái)考察不同的是,人類學(xué)者的民間信仰研究更多地是放在地域社會(huì)文化總體(人類)中來(lái)深描的,經(jīng)常列于結(jié)構(gòu)性研究系列中的一個(gè)部分。由于民俗志畢竟不能脫開(kāi)民俗(無(wú)論是民俗事象還是民俗生活)這個(gè)核心的界定,本質(zhì)上只有文化或民俗這個(gè)維度,故而在小地方或社區(qū)針對(duì)民俗整體的書寫,在表現(xiàn)魅力和表達(dá)深度方面難免就可能不如強(qiáng)調(diào)人的整體研究的民族志的深描了。后者恰因?yàn)橹粚⒚袼卓醋魇侨说恼w深描中的一個(gè)部分,小地方的民俗反而因此變得更立體化了。因此,民俗志有關(guān)民俗整體的小地方研究,又將如何避免那種可能將活態(tài)的民俗事象越做越小的境地呢?
換句話說(shuō),人類學(xué)的小地方研究,畢竟可以比較從容地從人設(shè)計(jì)社會(huì)或文化的各個(gè)方面,故足以讓小地方的人的整體呈現(xiàn)出來(lái);而民俗學(xué)在民俗的限定內(nèi)的小地方研究,在呈現(xiàn)人的整體方面終究有些艱難,因此難免瑣碎化的危險(xiǎn),從而可能導(dǎo)致這樣一個(gè)局面,即終究不能呈現(xiàn)地方民俗的整體,而只是呈現(xiàn)民俗在地方的一個(gè)切面。比如,比較民俗學(xué)者關(guān)于
妙峰山碧霞元君和莊孔韶《銀翅》關(guān)于地方信仰陳靖姑的描述,后者在體現(xiàn)并表達(dá)地方文化的整體關(guān)聯(lián)性方面無(wú)疑更富有魅力些。或者說(shuō),人類學(xué)的民族志的思考方式一直是非線性思維的,關(guān)于部分的相加大于整體,而不僅僅是部分的簡(jiǎn)單相加。而傳統(tǒng)的民俗事象研究取向常常帶有線性思維的特征,這當(dāng)然是弊病之一,但對(duì)于民俗學(xué)而言并非一無(wú)是處。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毋寧是如何強(qiáng)化民俗事象研究取向的非線性的思考。民俗整體研究取向堪稱是中國(guó)民俗學(xué)走向非線性思考的深化,但或許其終究要局限于民俗的本身,以及同樣陷入對(duì)歐風(fēng)美雨的癡情,故對(duì)于其他社會(huì)性內(nèi)容的關(guān)聯(lián)能夠就受到了限制,以至于這種只是針對(duì)小地方的非線性描述的魅力多少就打了折扣,以至于豐富的民俗事象的深描難免有細(xì)碎化的危險(xiǎn),以及重新喪失歷史感的風(fēng)險(x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