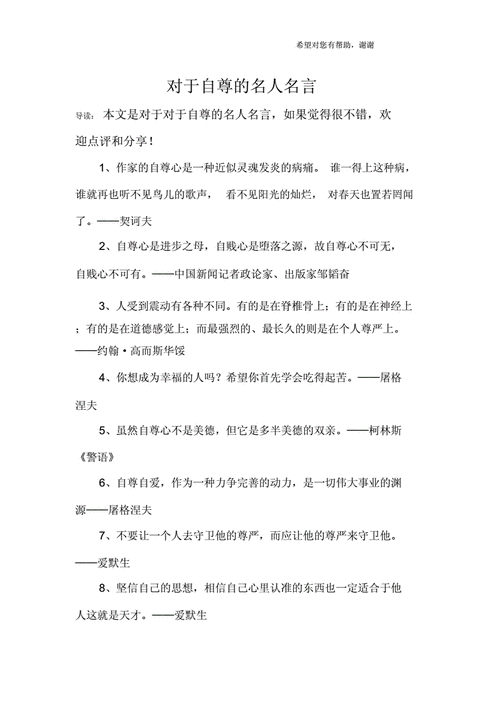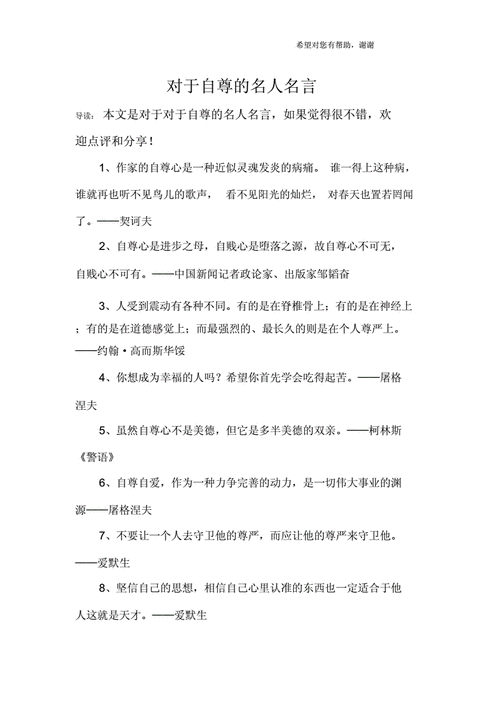
10000年中國藝術史讀后感
中國向來是個極重歷史的國度,然而“藝術史”這一門類卻是個新事物,一如“文學史”的書寫也只不過近一百年來的事,因為這本身需要一種現代思維。以前自然也有對藝術的批評、源流衍變的歸納整理,但那多不成系統,尤其是多只限定在某些特定領域的(如專論書法或繪畫),卻不會采用一種宏觀的回顧方式,按時間序列來討論從書法到繪畫、建筑、雕塑、陶瓷、織物、漆器等等在內的視覺藝術的總體面貌。
我們現在已經對這種藝術史的寫法習以為常,仿佛這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這其實代表著現代人對“藝術”和過往的全新認識。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史研究起于西方,這并非偶然,而我們如今對“藝術”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響。在閱讀這本書時,不應忘記的一點是:這本在歐美堪稱中國藝術史的教科書式的經典讀本,原本是寫給西方人看的,其中自不免滲透著西方對中國藝術的理解,其默認的潛在參照系也是西方藝術,它的創見與隔膜,在很大程度上都來源于此。
由于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國藝術品不斷出土,而對中國藝術的研究認識也日益加深,本書自1967年問世以來,在1973年、1977年、1984年、1999年多次重寫,而現在則是根據2008
年的最新版譯出的。大概沒有哪本《中國文學史》能盛行這么長時間的,這一方面固是因為文學史的書寫面臨的挑戰更激烈,但不容否認蘇立文的功底和與時俱進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這本《中國藝術史》的寫作架構乍看是最傳統的朝代框架,但這比起按藝術分類分別撰寫等方式更能給人帶來對中國藝術的一種穩定而連續的認識。
雖然注重對中國歷史的整體把握,但蘇立文拒斥那種激進的觀點,即“將藝術視為政治、社會和經濟勢力的表現”,相反,他是基于藝術本身來理解藝術史的。這既是對藝術自覺的強調,也是因為他無疑注意到,藝術和政治、社會、經濟的發展未必同步,有時王朝之間斷裂和混亂的時期,反倒出現了引人注目的藝術發展——堪稱中國最重要藝術的書法,就是在魏晉時期達到了藝術自覺,更不必說佛教藝術基本是在五胡亂華的亂世中醞釀和成熟的。因此,他在撰述時,基本只將政治、社會作為藝術發展的一個情境,但注重的仍是藝術自身脈絡中的演變。
作為西方人,他不難注意到中國藝術的獨特性,而這最終又只能歸結為中國思想的獨特性——特別是那種強調自然的形態和模式,這在山水畫中表露無遺。如果說西方的藝術以人物為重心,草原藝術以動物形象為主,那么山水畫所表現的則是自然世界的精氣。值得補
充的是:中國的山水畫與西方的“風景畫”乍看相似,其實在精神本質上卻不是一回事,因為西方以透視法畫的風景畫仍始終假定有一個人在外部觀看、主宰這個畫面。不過,可能也因為潛意識里將山水畫視為中國畫的代表,蘇立文在這本書中對傳統中國繪畫中的人物、花鳥的著墨要少得多,以人物畫著稱的陳洪綬,僅在任伯年再現其古樸風格時提到一筆,而明代徐渭開創的大寫意花鳥則根本未置一詞。